地址:
广州市珠江东路4号
邮编:
510623
网址:
www.gzlib.gov.cn
总机:
(020)83836666
邮箱:
dzyj@gzlib.org.cn
传真:
(020)83340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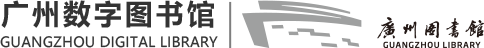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