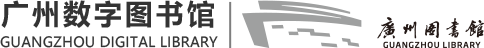来源:南方都市报
.jpg)
艾云在湘西凤凰城留下的近照
.jpg)
大学时期的艾云
女作家艾云的脸上,永远带着淡淡的笑容,她穿着很有品位,举止优雅,甚少人见她放下高挽的发髻。她给记者与几个年轻的朋友讲述当年高考的旧事,末了,璨然一笑;说道,想不到吧,我曾是个烧窑工。当年,这个在烧窑间隙还会从裤兜里掏出鲁迅的书看的女孩子,高考是她走入文坛的第一步。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和要好的五位同学,沈影、周朵、黄芃、常虹到河南省中牟县狼城岗乡插队,在不同的村务农当知青,幸好相距不远,有空可以常走动。我们白天上工,做的都是大男人的活,辛苦自不言说,但也挺过了三年。
不甘落后相约复习。
1977年麦收结束,过完端午节,回城歇了几天的知青又纷纷回到插队小组了。周朵自打回来,就开始不声不响地趴在床边演算做题。后来她告诉我们,上边已经有确切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不用层层推荐,人人都可以报考。她说她的消息来源比较准确,因为她哥哥周洪留城在河南大学的校办工厂。她说现在得抓紧时间复习了,可能年底就要考试。她正在做的是几何、代数题,从初中课本开始,每天都给自己规定题量。我和沈影将信将疑。我们曾经有过大学梦,但“张铁生白卷事件”之后,教育部门已关了死闸。我们只想有朝一日可以回城,能去卖菜卖肉站柜台或当服务员就很不错了。
夏收过后有一段反倒农活不忙,上工晚,下工早。太阳还没落山,我们就开始到别的插队点儿串门了。我们住在村西头的大队种子实验场,可以遥遥看到二里半地远的太平堤东头的知青点。常虹是我们的同学兼好友。那晚,我和沈影、周朵去常虹那儿,她也在复习功课,她的父母都是高中教师,也得知有恢复高考这事。我们就有些坐不住了,看看天色还早,就索性走七八里地去看朋友黄芃。黄芃父亲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然也知道些信息,于是,我们五个女伴开始计划复习功课了。
课本找不全决定考文科
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在1977年八九月份成为大道消息,许多知青都已回城复习了。我无法请假,因为这时我已从窑厂被抽到村里的民办学校教书,并担任班主任,有课有学生,一时半会走不脱。业余时间开始看初高中课本了,找不全,大部分都丢掉了,没法做数学等习题,我决定报考文科。
我之前还是有读书习惯的。在窑厂干活那会比当民办教师辛苦多了,当时烧窑是手工脱胚,然后人工装胚,烧成砖以后还要上到窑顶浇水才能成为青砖。浇过水晾些时候,又得钻进窑里一行人排着队轮替着接手出砖。在窑厂干的都是体力活,但歇息的时候,我会从裤兜里掏出鲁迅的书来看,《彷徨》、《呐喊》、《而已集》及《两地书》都是在那时看的。
秋天里,大队通知我们到公社填报志愿,考试定在是年年底,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随后我们基本上都回城复习了。很多日子没有摸过课本,猛地要复习,滋味不好受。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看书,北方屋子里有煤炉粉尘,让人常常头疼,但也得硬着头皮看。除了自己看书,晚上我们会到不同学校去听高考辅导课。听课不收钱,多少年来没有听众的老师们觉得自己此时大有用场,业余辅导课他们个个神情激动,帮助我们划重点,猜题目,串讲破题,却又分文不收。
我们五个女伴家住得都很近,早早吃了晚饭,结伴就去听课了。我们母校八中大袁二袁老师,一个教代数,一个教几何,讲课特棒。她们姐妹俩是北大毕业,人清爽、芳馨,常常是白色丝巾揽在脖领,飘逸又超尘。但我们都听说她俩早就抱定独身主义。她们的确是终生未嫁。我们去听她俩的数学课,然后,又过铁路,再过曹门城墙,到很远的十中听史地课。
巧遇熟悉的作文题目
临近高考,我们提前回到乡下,然后找到正好要到县城运货赶马车的晏明,他同意我们坐他的马车到县里。北方乡下12月已经很冷了,马车上堆放了很多货物,我们高高坐在上面,冻得发抖,一路颠簸到了县城。虽说高考知青安排有大通铺可以住,但我们还是自己找到了接应。
在县一中的考场考了三天。我仍记得自己的语文考得不错。那年河南省出的高考作文题其中有“我的心飞向红主席纪念堂”一题,是记叙文。我一看题目,马上就洋洋洒洒写开了。为什么这么顺呢?说来凑巧,我在当民办教师时,就在办公桌底下发现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有一整版长文报道,文中写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用极快的速度建成毛主席纪念堂。
那篇长文用了华彩斐然、叠床架屋的形容词描述毛主席纪念堂。我看时就把浓词艳句抄摘下来了。高考作文题出得正合吾意,先是许多句子跳出来,然后做了结构和剪裁,一篇扣题很紧的作文就出来了。那时尚有赶不去的“文革”遗风,写文章都特别喜欢强烈套饰、高调抒情。
而常识部分,有一问答题是对当年鲁迅关于“费厄波赖应该缓行”怎么理解。也真是碰巧了。在周建新家里住的头天晚上,她床头放了高中语文课本,我随手翻时正好看到这一篇,里面的意思是痛打落水狗云云。
五朵金花同被录取
考试结束,开始回到插队点。等消息的这些日子,我们每天晃晃悠悠,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找知青串门闲逛。村里人也知道我们早晚要飞,也不把我们当劳力看了。我很担心,考不上连民办教师也做不成。晚上,在黄河大堤,裹紧毛衣,吹着口琴,心里满是虚无。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吹口琴。
终于等来了通知书。我们五个女伴全部都考上大学。沈影考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黄芃考上西南交大,周朵考上河南大学,常虹考上开封大学,我考上郑州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插队点另外几个男知青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却是落榜。他们再复习了半年,1978年夏季考试时,小冰考取华中师大中文系,小敏上了北京大学地理系,小末上了北京师大化学系。他们第一次没考上,来年考上那么好的学校。如果我和他们一样,我是否会上一所更好的大学,命运有更大的不同?不去想了。总之,我们没有经历熬蒸般的复考,能在十年里第一次恢复高考时就被录取,已是满足。当然,身份与命运也由此而改变了。
口述人:艾云
女,1957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开封人。1974年赴中牟县狼城岗乡插队务农,1977年考取郑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历任河南省文联《莽原》杂志编辑,广东省旅游出版社编辑,广东省《作品》编辑,副编审,一级作家。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著作十余种。《用身体思想》一书获广东省政府“鲁迅文艺奖”理论著作奖。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方夷敏刘丽君
本版记录:本报记者邱永芬
图片由口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