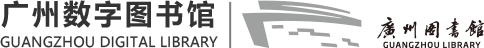光塔高耸。
广州有条光塔路,光塔路上有一座塔。
这座塔不是中国传统的宝塔造型,而是高耸入云的圆筒状,朴素又敦实,带着股豪气干云的倔强气质。
它的异域风情,透露了它不寻常的来历。千百年前,当这尊塔所俯视的光塔路一带还是一望无际的珠江边之时,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蕃坊”。数以万计来自大食和波斯的“蕃人”,带着璀璨夺目的珠宝,带着香气四溢的香料,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在光塔下栖息,和广州人做生意……他们很快适应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学习这里的文化,并且和广州人通婚,生下一代又一代的“土生蕃客”……渐渐地,他乡变成了故乡。
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于是他们在江边建起进行宗教活动的清真寺和高高的光塔。每个白天,光塔上“邦克”的声声呼唤,给这些背井离乡游子的心灵指引着方向;每当夜幕降临,光塔上高悬的灯光,又在指引着海上的船只,朝着这个陌生而富饶的国度,风雨无阻地前行。
像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事实上,在这部反映中古时期阿拉伯趣闻的世界名著里,那位名为辛巴达的航海家,他的原型——阿曼航海家阿布·奥尔达,于公元750年从现在的阿曼苏哈尔港起航,漫长航程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广州光塔路一带。
一千多年以后的光塔路,那些已经无从寻觅的奇幻往事早已隐身而去,空留寂寞的光塔路,如一个默默无言的舞台,承载着曾经的辉煌。今天,让我们重新扣响“芝麻开门”的问询,去找寻光塔之下千百年来的故事传说。
海上丝绸之路
万舶争先进大唐

展厅里反映当年海上丝路盛况的油画。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当中国广大地区还处在未开发的榛莽状态的时候,当时称为番禺的广州,已经开始了自己海上贸易的历史。
广州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贸易大港。一条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的“海上通道”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它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三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是当时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大食人(今天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今天的伊朗人),就是沿着这条海上之路,不远万里来到广州。当时的盛况,如今想来简直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神话场景。
因为唐朝实施开放政策,广招海外商人,所以内外商旅、各国使节都从广州出入。据阮元的《广东通志》记载:“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海泊“种极多”,“不知其数”,“大舶参天”,“万舶争先”。
用现代广州人的思路来推想,那“夷人随商翱翔城市”、“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兴旺景象,估计就相当于“广交会”的状况吧,只不过,这场特殊的“广交会”,持续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会。
“蕃坊”的创立
唐玄宗时曾经两度下诏禁止互市,封锁了陆上交通,断绝与西域的经济往来,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来来往往却因此变得更为频繁——更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由海路前来,他们聚集在广州,与中国商人交易货物,广州在那个时期成为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这些纷至沓来的外商中,以阿拉伯人为最多。他们把广州人称为“新卡兰”,意为大中国。今天惠福西路坡山巷原有一座高丘,称坡山,山下有一天然石穴,状如脚印,世称“仙人足迹”,古珠江就是从这里悠悠流过。而当时位于此的“坡山古渡”是唐宋年间广州最大的码头。从波斯湾远道而来的船只大多在此靠岸。那些人生地不熟的异域商人上了岸,一时半会走不了,便就近驻扎下来。古书记载这些侨民“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天长日久,渡口附近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朝廷终于决定,就在这里设置专供外国人(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的社区——“蕃坊”。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涉外的国家、事物都冠以“蕃”称。在广州话里,这一称谓保持至今。究其来由,估计要到《周礼·秋官·大行人》里去找解释:“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也就是说,当时除了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等州之外,其他的地方就都是“蕃”了。
从设立蕃坊的那一天起,朝廷同时设立了“蕃坊司”和蕃长进行管理。“蕃坊”内还设有“蕃市”和“蕃学”。“蕃市”供侨居的外商交易。“蕃学”是应蕃人要求,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中国文化。
《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述了元朝时期广州蕃坊的情况:“广州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即阿訇,一个地方的总教长),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一般来说,历来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明显“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情况,是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的教权组织制度的一种体现。
蕃坊的主持叫蕃长。他一般由穆斯林公众选出,然后经政府的审批与任命。蕃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所担任。他的职责是管理蕃坊内部的一切事务,特别是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来华贸易。如果穆斯林之间产生纠纷,蕃长也要负责调解。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蕃坊,基本上相当于现在领事馆的性质。
“蕃坊”今昔
光塔路原名大食巷

怀圣寺院内。
根据记载,广州的蕃坊位于广州城南,呈长方形。以光塔路为中心,南临珠江之滨,东至朝天路、米市路,西达太平路(今天的人民路),北抵惠爱西路(今天的中山六路)。蕃坊一共占有马路、街、巷、里等十二三条。几百年过去,那些曾经在这里摩肩接踵的异域客,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从光塔路附近一些小巷的名称,窥到一丝过往的痕迹:
光塔路原名大食巷,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大食人(阿拉伯人)聚集之地。它对面有条小巷叫仙邻巷,其实“仙邻”是阿拉伯语“中国”的音译。
这里还有个玛瑙巷,不言而喻是蕃客在此地经营珍珠玛瑙而得的名称。玛瑙巷走到尽头是中山六路,向西可以转到擢甲巷,“擢甲”其实是阿拉伯语“小巷”之音译。走出擢甲巷即转入海珠中路,其南段原来叫“鲜洋”街,即阿拉伯语“送别”之意,唐朝要求广东地方官府对离开外国商人一律举行宴会饯行。
那片地图上曾经保留着的蓬莱北的地名如今找不到了。蓬莱是伊斯兰教做礼拜之前的唤礼词中“真主至大”的音译。
“蕃商”在广州
那时候的广州人,应该是中国最先接触到“老外”的一批人。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客,他们无论是语言、长相、服饰、生活习惯都和我们相差甚远。对异域风情的接受自然需要一个过程,在有关蕃坊的古籍中,“友邦惊诧”的记载着实不少:“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宋·庄绰《鸡肋编》)
“恂曾于蕃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砂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唐·刘恂《岭表录异》)
“其人手指皆带宝石,嵌以金锡,视其贫富,谓之指环子……最上者号猫儿眼睛,乃玉石也……”(宋·朱彧《萍洲可谈》)
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蕃客们于广州的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蕃商到广州经商,发财的不少。宋朝苏辙在《龙川略志》里记载:“蕃商辛押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明末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则说:“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
慢慢地,他们开始学习接受这里的文化,把孩子送到华人学校里去学习。南宋龚明之著的《中吴纪事》里提到:“程师孟知广州,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南宋的《铁围山丛谈》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
其次是婚嫁。《新唐书·卢钧传》里说:“蕃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甚至说,“五代时国主喜纳波斯女,而宋时宦族亦爱嫁大食人。辽时大食国王请婚,亦曾以公主嫁之……可见五代辽宋时与回回通婚一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阿拉伯、波斯商人与广州土著居民的结合,产生了他们混合的第二代,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土生蕃客”。他们有的住唐五年、十年,有的一直住到宋代,长达数十年。由于宋王朝的重视和鼓励,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的势头更加如钱江潮涌,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与日俱增。他们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根据统计,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的时候,已经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为此,宋政府还特意颁发了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以解决他们在华的遗产分配问题。这些土生藩客在广州,就成了广州回族的原始成体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掺杂了当时非中原人的其他地区的商人后代。
作者:金叶
上一条: 怀圣寺 中国第一座清真寺
下一条: 岁月风云陈济棠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