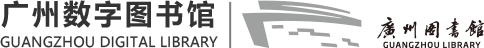摘要: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jpg)
骆以军在书房。
骆以军
1967年生于台北。台湾中生代代表作家,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团》、《妻梦狗》、《第三个舞者》、《月球姓氏》、《遣悲怀》、《西夏旅馆》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大专青年文学奖小说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红楼梦奖等。
“那里像是‘恶心’的拾荒老人地下室。”骆以军这样形容自己在台北出租屋里的书房。
.jpg)
骆以军会用电脑,但写稿还是习惯用A4纸手写。
确实如此。这里不到五平米吧,天花板的吊灯给室内覆上一层柔黄色,穿过中国木雕式窗棂的日光恰好落在窗边书桌。桌上高垒的书、稿纸和其他资料已有近一年未整理,杂乱无章,几乎要把写作者整个上半身挡住。
一堆堆书籍凌乱地摆在两边墙上的书架中。房内除了书几乎没有其他摆设,许久前贴在墙上、用来记录写作灵感的便条贴已洒满灰尘,现出暗黄色。
这里是小说的世界,尤其是西方现代小说,放眼望去都是小说。之外,显眼的是一摞西夏史———六年前,刚开始写《西夏旅馆》的骆以军从深坑搬来台北,好友黄锦树帮他找到不少大陆出版的西夏史书。
.jpg)
客厅中的书架上,贴着12岁儿子写的对联,书架右下角摆着一套父亲在戒严时期购买的《鲁迅全集》。
跟台北许多作家如唐诺、朱天文一样,骆以军常背着书包到台北温州街的咖啡屋读书、写作。“所以说,这个书房对我意义不大,我的书房是‘流动的咖啡屋’。”骆以军把书房比作“练功房”、“工房”,“我不是文人,是职业运动员。写小说是高度专注地锻造,不是修身养性。”
骆以军非常尊敬前辈作家朱天心,朱天心曾到他深坑的书房参观。当她看到“满目的书之山谷”,顿时安心。“原本她怕我因生活压迫而没有写作状态,可看到这打铁匠的炉灶还是热的,就放心了。”
这里堆满的极不规整的书,在骆以军脑中有着内在的逻辑。有几次岳母帮他整理了,却让他再也找不到某本书。
骆以军说,同是“混乱不堪”,他在深坑的书房世界却更为广阔,有诸如变态心理学、鸟类学、人体解剖学等冷门的工具书。他说想起深坑的书房岁月,有点怀念和感伤,“在不用赶稿子的时候,可以幸福地读读这些工具书,多么幸福。”
读书:像海绵一样吸
骆以军的父亲是中文老师,家中的书大部分是父亲收藏的经史子集。还是男孩时,骆以军常常被关在家里,翻看父亲书房中像“电动世界”的演义故事,包括《西游记》、《东周列国故事》、《朱洪武演义》。又或在姐姐的书柜里遇到朱天心的《击壤歌》。他偶尔也到小巷子里的书店,读司马中原的小说,“里头有狂风沙、北方的英雄好汉。”
直到高四复读那年,每天只想翘课的骆以军,对文学有了真正的饥渴。他无意中读到余光中翻译的《梵谷传》(台湾将凡·高译作“梵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痴似的激动”,他用典型的骆式口吻表达当时的亢奋心情:“我要当艺术家!”他回忆,后来遇到不少台湾艺术家都说深受此书影响。《半生缘》也让他激动。骆以军说,张爱玲描写世均对曼祯告白时的街影,让他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就想,如果我可以把这整本书背下来,我也可以写东西了。”
从1949年到1987年是台湾戒严时期,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的苦闷,台湾文学很大程度受到英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时,新潮文库书局、志文出版社出了一系列存在主义文学,像骆以军这样的60后,在饥渴的青少年阅读年代,几乎人人都深受卡夫卡、加谬、萨特等作家的影响。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在此前后左翼文学书籍通过各种小书店进入台湾读者的视野。骆以军终于在鲁迅、茅盾、萧红等人的笔下,“更真切地感受到外省籍父亲口中的那个大陆原乡。”
骆以军至今记得,大学第一学期的冬天,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宿舍,窗外漫天大雨、雾气迷蒙,他把自己埋在书堆里,“用功”地抄写着卡夫卡的《城堡》、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因为看不懂那些艰涩文字”。意外的是,他一口气读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那些哲学辩证实在太好看!”
.jpg)
朱天心长期鼓励骆以军写作,赠其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上面题字“无论未来会如何,我们约好了要幸福开心喔。
“比起台大毕业的同行,我的阅读缺乏理论的逻辑结构,只像海绵一样吸。”骆以军甚是怀念那一段朦胧的“爬生类梦境”般的阅读体验。
那时为了买书,他穷得要命,穿着邋遢,是校园中“人渣中的人渣”。一次拿了一笔小小的文学奖金,马上跑去买了光复书局出的《世界小说家读本》“还是盗版的。”
骆以军大部分的小说阅读集中在了十九岁到二十六七岁。进入研究所后,因为念戏剧系,他也读一些理论。他很少读诗歌和散文,因为他认为小说是万王之王,是所有语言的综合,“小说几乎就是世界。”他把自己对阅读的追求,比喻成小说《香水》中,那个有点变态、不顾一切索取各种层次感味道的格雷诺耶。
写作:冷酷的现代主义
在广阔的语言世界里,骆以军体验到了东西方世界不同的混杂经验。
他抄写王安忆、莫言、阿城等大陆作家的书,不由感叹,“那些中文对我来说是练字。在当时的台湾,古文课也很难补上足够的中文底子。”而他在大陆小说中感受到更具有生命力和表情的语言。“像张爱玲书中的某个段落,细光垂下来,一个转景,人淡淡的。”
更让骆以军羡慕的,是大陆文学中的一套农民经验。他提到李锐的作品,“都是活生生的字,比如描写牲口。”还有阿城,“只是描写牛过铁链桥,但读每一个字都像吃东西,千滋百味。”
大部分时候,骆以军沉浸在现代主义荒谬而冰冷的文字世界中,大陆文学作品中“放牛羊”的感官经验是他在生活里万万体会不到的。“关于原乡的记忆只停留在客厅父亲的故事及这些文学中,我是失去了。”
阅读的感受渗入他的写作中。从《红字团》到《西夏旅馆》,骆以军的作品所释放出的气息也充斥着现代性的疏离。“二十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没有快乐的,整个现代主义就是在垮掉。”他说,创作者就是整个人类噩梦的接受者。
三十岁后,骆以军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套拉美文学丛书,花许多时间将整个拉美文学系列认真读了一遍,并慢慢了解到文学背后的历史社会脉络。
在骆以军心目中,阿根廷小说家波赫士(即博尔赫斯)是二十世纪小说家第一名,“他创造了几何式的、天文学式的小说结构”。同样对他的创作有着巨大影响的是卡尔维诺,“《命运交织的城堡》立体的小说语言排阵。”骆以军新作《西夏旅馆》要建构的也是类似的动态迷宫。
过去几个月,骆以军为了宣传新书,忙于参加各种讲座活动,直到最近重新回到咖啡屋里享受读书之趣,他最近看的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和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这么多年,他仍是习惯性地边读边抄。若遇到个大嗓门的邻桌,他就收起书包,起身走人。
撰文:钟瑜婷 摄影:游胜富
上一条: 张柠 迁徙三千公里的书房
下一条: 黄锦树:山下自有“黄”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