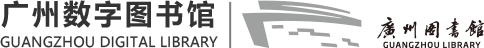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jpg)
.jpg)
北京路一带的越秀书院街,那里曾集中了十几家古书院,其中就有叶衍兰一手创办的越华书院,现
在只有从牌坊上还能闻到些许书香味,许多房屋墙上还写上了大红的“拆”字。本报记者 邹卫 摄
家族大视野
王侯将相宁无种乎
1948年,风雨仓皇之际,“学衡”派旧文人吴宓徘徊在汉川之间,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像老友陈寅恪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思忖,“当局可以改变其笔与口,讵能改变其心耶?”言下之意,自己是不必改造的,也是不可改造的。
吴宓显然看轻了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术。此时叫得最响的,便是陈胜当年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为“另一个阶级”的旧文人,吴宓即使不在“王侯将相”之林,也在“才子佳人”之列。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王侯将相”与“才子佳人”都已无遁迹之处。新政权的改造方式被惯称为“洗澡”,通过发动群众,让被改造者根据其职位高低、名声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集会上公开地、反复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最后由群众决定其是否“过关”。这种改造方式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旧时代知识分子高傲、骄矜、自尊的心理特性,通过深挖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来消弭其心理上的道德优势,从而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
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改造,吴宓终有所悟。1950年底,吴宓作有《感事》诗五首,感怀身世,总述入川以来个人之心境,寓自伤之意。其中第四首写其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诗曰:“变征移宫怨柱移,琵琶别抱态羞迟。半生清节科新罪,千古高文系旧痴。洗髓刳肝难焕骨,绝情弃智强陈词。青衿满座绳吾短,最苦身犹作教师。”“变征移宫”亦作“移宫换羽”,谓乐曲换调,喻事情起了变化。以“羞迟”之态接受满座青衿的“洗髓刳骨”般的“强陈词”,滋味自是不好受,即便如此,他对那种“唾面自干”的做法依然不能接受。吴宓认为,自己是属于“不可改造者”之列,而非“不应改造”,既带有深深的“原罪”,又“不工巧言伪饰”,其结果就只能是引颈就戮了。因此,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吴宓便“深自危”,多次说自己“将死矣”。
1954年春,吴宓作《已衰一首》,此时,他来重庆已是六年整。诗云:“已衰无志畏名身,甘隶新邦作幸民。未敢说经陈异义,尚容分俸济同仁。葫芦依样难工画,傀儡登场讵肖神。六见嘉陵春水绿,诗书尽废梦成尘。”此时已甘于“作幸民”的吴宓似乎有些意志消沉了,不仅不敢“陈异义”,而且还“诗书尽废”,自己聊以存世的精神寄托都已“梦成尘”,岂不悲哉!吴宓期待“早死”也不是偶然的,他已预感到以后的岁月将更不好过。
“文革”期间,吴宓惨遭批斗,被打折了腿,直至被家人接回,终老故土。三十年的改造生涯,虽最终未能收服吴宓的心,却给他制造了巨大的阴影和灾难,弥留之际,他犹自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这位标本式的世家子,正是依靠一种传统文人深厚的精神和生活积淀,秉持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良知,才在“革命的洗礼”面前,没有作恶,没有帮凶,没有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 □ 朵渔
历史的枢纽
身在官场,不失书生本色
叶衍兰曾经先后担任过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叶恭绰官至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公超是外交部部长,但尽管如此,叶家几代人留给世人的印象还是能写能画,是典型的文化世家,而非官宦世家。
叶家家学渊源深厚,叶家子弟又勤奋好学,他们中不乏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奇才”,但似乎都不会做官,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人,归隐田园不说,还被限制了自由。
曾经有一位地位显赫的皇族私访叶衍兰,落座后就抽起旱烟来,屋里很快烟雾缭绕,从不吸烟喝酒的叶衍兰叫佣人打开窗户,无意中得罪了权贵,官场中那一套虚伪的应酬交际并不符合他的性格,最终他选择了辞官回乡,在广州开办著名的越华书院,讲学长达40年,桃李满天下。
叶公超更是一性情中人,身为“外交部长”,他居然请美国大使吃小摊,他最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吃蒙古烤肉,喝金门高粱酒,兴致来了,就唱一段京剧《打渔杀家》,他最看不起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情报贩子,最痛恨小人得志,打击正人君子。
叶公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道,“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虽然没有点名,可谁都明白其中的某某就是蒋介石,他甚至敢当面和蒋介石顶嘴,“别的你懂,外交你比不上我!”
书生意气的结局是他被迫黯然离开外交界,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只好寄情于书画中,闲而狩猎、感而赋诗,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
虽然为官多年,但除了薪俸,别无来源,叶公超的花销又很大,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一个学生祝贺他出任“驻美大使”,他却俯在学生耳边轻轻地说,“不用提了,赔钱货!”叶公超经常靠出卖古玩、古籍、字画甚至自己的墨宝还有“外国大使”送的名表为生,两袖清风的他连晚年穿的皮鞋都是打过补丁的。
正如叶公超所说的,他不记日记,不收集照片,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他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幅漂亮的画、一首清新的诗都会比那些虚位官名更让人无法忘却。
后世回忆
叶家是文化世家,最早在17世纪中期就开始收藏。一位中国书法权威学者形容叶家的书法收藏为广东四大书法收藏家之一。2003年,叶公超的女儿将叶氏家族的135件书画藏品全部捐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批作品是叶家五代人的珍藏,最古老的藏品可追溯至七世纪,最近的则有张大千、溥儒(心畲)、赵少昂、黄君璧、于右任及叶公超本人的书画作品等。
叶家珍藏寄存在美国
1958年,时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获蒋介石“总统”的任命,接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当年9月10日,他搭乘华航班机赴华府履新。“大使馆”就在“双橡园”,叶公超将自己历代家族的书画珍藏携带来美,用来装饰“双橡园”。
1961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有关外蒙古入会案问题,叶公超和蒋介石意见相左,虽然最后蒋介石同意将外蒙入会问题,由投票“否决”改为“弃权”,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造成伤害。当年10月13日,叶公超紧急奉召返回台北后,丢了“驻美大使”职务,改调无“务”可“政”的“行政院”“政务委员”,并被禁足不准踏出“国门”长达16年。
叶公超奉召返台时,以为很快地就会回到华府,因此只携带简单的换洗衣物,其他什么也没带,当然更不会事先处理在“双橡园”“大使馆”内的叶家书画珍藏。不能回美后,他无法亲自处理这批书画,后来由馆里同事将它们寄存在银行的保险柜。多年后,再由儿子叶炜将书画寄存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那尔逊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在捐赠给亚艺馆的135件书画中,属于较早期的书画,是寄存在那尔逊博物馆多年的一批(另有青铜器等文物则留赠那尔逊博物馆),但近代的书画家作品则是由叶彤、叶炜在父亲过世时返台参加葬礼后,整理遗物时携带来美的。
叶家的这批珍贵书画收藏,从“双橡园”搬出,存放在堪萨斯那尔逊博物馆的贮藏室后,多年不见天日,也没有展出。亚艺馆贺利回忆说,大约七八年前,堪萨斯大学美术史教授李铸晋特别就叶家这批字画珍藏,建议旧金山亚艺馆应争取收藏。后来,叶炜寄来了李铸晋、香港书画鉴赏家黄君实及那尔逊博物馆东方馆馆长杨晓能博士等观赏叶家这批字画的现场录影带。
张大千为她画猫
叶公超与张大千生前是好友。1938年,叶彤5岁时,有天她父亲跟她说:“走,去看住在山洞里的张伯伯(张大千)!”她记得,好像坐了好久的车子,才到一个地方看到张伯伯。张伯伯和她父亲聊了一阵子后,问她说:“张伯伯给你画个东西,你喜欢什么?”她父亲在旁说:“画猴子!”她摇头说:“不要,我要猫!”
张大千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三两下就出来了,送给她一幅《髦耋呈祥图》:画中只有一只猫。这幅画后来又增加她叔公叶恭绰的题字“且随蝶共舞,莫与鼠同眠”。叶彤说,这可能是张大千唯一画的一只猫,且是赠送给她的,她保留下来,不在捐赠之列。不过,亚艺馆在出版的《雅集:叶家书画珍藏》的图录中,也将这幅画包括在内。
叶家藏品属中华文化
叶公超于1981年11月20日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叶家这批字画珍藏在堪萨斯那尔逊博物馆的多年期间,叶公超的公子叶炜也试图与美国各大博物馆接洽,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内,试探他们是否有典藏的意愿。叶彤说,有些博物馆只愿意收藏当中的几件作品,并不愿照单全收。而这一条件正是他们两姐弟最坚持的,叶家的这批珍贵书画收藏,必须永远在一起。
叶炜接受主流媒体访问时曾表示,如果将这批珍贵字画收藏分件卖出,他和姐姐叶彤至少可以得到好几百万美元。但他们决定捐给亚艺馆,让这批字画在一起,不流散,日后可以供学术研究用,意义更重大。
亚艺馆自1966年成立以来,在中国艺术品收藏方面,大多属瓷器、雕塑等器物,字画作品收藏较弱。贺利说,叶家这批珍贵收藏,正好弥补了亚艺馆字画收藏的不足;在叶家方面,则为他们几代的收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华人认为,凡属中国的文物珍藏等,都不该流出海外,已在海外的,甚至应该追讨回来。叶彤说,曾经也想到将叶家珍藏捐赠给北京故宫或台北故宫博物院,但因为她叔公叶恭绰的书画收藏,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大半被毁,现在剩下来捐赠出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台北方面,他父亲叶公超生命中最后的20年,在台北有志不能伸,且一直在情治单位监控下过日子,直到他过世。她觉得,将叶家珍藏捐赠给国外的博物馆,是最安全的做法。
叶彤说,她没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叶家书画珍藏,虽属个人家族收藏,但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由旧金山亚艺馆永久典藏,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机会认识精致、珍贵无可比拟的中华文化。
.jpg)
叶恭绰
.jpg)
叶公超
.jpg)
.jpg)
叶公超所画的兰与竹。
.jpg)
叶恭绰捐建的仰止亭。
□ 家族谱系
1 叶谦亨(六世祖)祖籍浙江余姚,因游牧广东,举家南迁。
2 叶仁厚,叶谦亨之子,书画诗文都有成就,著有《巢南诗钞》。
3 叶英华,字莲裳,叶仁厚之子,叶衍兰之父,叶公超的高祖,工诗词,善花卉、人物,与汉军子璞郡丞(秀琨)诸人结画社,有题自画拜月美人词,著有《斜月杏花屋诗钞》、《花影吹笙词录》、《庄严馆随笔》等。
4 叶衍兰,字南雪,号兰台,叶英华之子。咸丰六年(一八五六)进士,官军机章京,直极垣二十余年,后主讲越华书院。工小篆行楷,精于绘清代学者遗像,各附以小传,自顾亭林至魏默深凡百十七人。其孙恭绰,为影印传世。又摹陈其年填词图,清微道人空山听雨图等。著秋梦庵词、海岳楼诗。弟子昌广生、潘飞声等皆以诗名于时。
5 叶恭绰,叶衍兰之孙,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18年到欧、美、日、朝鲜诸国考察。1920年,支持金城、周肇祥等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1923年应孙中山召,至广州任财政部长。1925年转而做文化组织工作。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由叶组织筹办了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提议并组建了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规模影响及权威性皆称一流的全国性“中国画会”。1933年创建上海博物馆,并担任多种国际机构领导职务。抗战时一度避居香港,以卖字为生。建国后,历任北京画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6 叶公超,叶恭绰的侄子,曾经就读于英美等国,回国后曾先后任教北大、清华及西南联大。1940年,在董显光先生的推介下转入外交界任职,而在1961年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突然被召返,旋被免职,并被禁止出国长达16年,他被迫离开仕途后,重拾文学、艺术嗜好,寄情于书画,怒写竹、喜画兰,1981年在台北逝世。
□ 专家视角
叶恭绰的脑子就像一个货仓
受访人: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人们言及叶恭绰的时候。一般会直觉地认为他是交通系领袖、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实际上,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文史专家,用“天才”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才能智慧,实在一点也不为过,他曾经这样表述自己,“我一方面在讨论工业技术问题,同时却可以谈谈宗教、哲学,一方面研究一个公司要怎样组织,同时又会想到音乐、书画上的问题;而且似乎不会混乱。”所以,老友冒鹤亭常说,“叶某的脑子大概像一个货仓,把各种货物分类的存储,要用时,一样一样取出。”
□ 地理记忆
斯人已去,遗迹难寻
叶家的籍贯虽然是在广东番禺,但叶恭绰和叶公超都是千里做官,四处漂泊,叶公超死在了台湾,叶恭绰的墓地却在南京中山陵。
叶恭绰敬重孙中山先生,誉其为“中华民国第一伟人”。1930年初,叶恭绰向孙中山陵园筹建委员会捐了五百银洋,建议建一纪念亭,并取名“仰止”,取之于《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义,是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崇仰之情。仰止亭是陵园内唯一一座由个人捐建的纪念性建筑。病危中的叶恭绰曾经表示:“我追随孙先生多年,希望死后能葬在仰止亭旁边,在九泉之下也能见到孙中山先生。”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绪柏告诉记者,广州市内与叶家有关的遗迹就只有叶衍兰一手创办的越华书院了,记者来到位于北京路的越秀书院街,那里曾经集中了越华书院、禺山书院、粤秀书院、庐江书院、西湖书院、羊城书院、濂溪书院、考亭书院等十几家古书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古书院群落,但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座牌坊,而古书院群落的旧址上则写满了大红的“拆”字,行色匆匆的女子从巷子里匆匆走过,开发商已在这里跑马圈地,一座新的高楼正要拔地而起。
□ 家族逸事
叶恭绰与张大千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碑帖很吃香,价位十分坚挺,所以号称“黑老虎”。张大千祖传的王羲之所书《曹娥碑》帖,就是一头赫赫有名的“黑老虎”。但它竟被当时年轻嗜赌的张大千输掉了,10年后,张大千的母亲、女画家曾友贞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祖传的《曹娥碑》帖。张大千惶恐已极,只好撒谎说仍放在苏州。其母叫他第二周必须带来展阅。张大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张大千将自己输掉碑帖的经过也一一陈述,没想到《曹娥碑》帖竟然辗转流传到了叶恭绰那里,张大千表示愿意用自己所收藏的历代书画,不计件数地任叶挑选,以为交换,叶恭绰义形于色地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赠给大千,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张大千和张善子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刻上前叩首相谢。张太夫人终于在弥留之际看到了祖传的唐拓宝帖。
叶公超的另外一个“爸爸”
叶公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在九年七个月的外交部张任内,完成了两件影响历史的大事:第一是签订了《中日和约》,第二是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奠定了台湾三十年的安定局面。
叶公超学贯中西,文采风流,他具有文学家的气质,外交家的风度,艺术家的鉴赏能力,他说话坦率而风趣。他常说:“见大人,则藐之。”因此他于驻美大使任内,在拜见艾森豪威尔时,内心把对方当成“大兵”,与肯尼迪会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个“花花公子”,一个小开而已;另一方面,他对小人物非常客气与容忍,下面就是一个实例。
有一次,叶公超打电话找中国邮报发行人余梦燕。
接电话的工友说,“她不在,请问您是那一位啊?”
他说:“我是叶公超。”
工友以为他在胡闹,于是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爸爸。”
叶公超停了一会,幽默地说:“爸爸!请你告诉我余梦燕在哪里好吗?”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许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