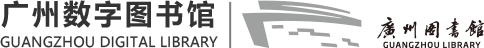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jpg)
邓圻同坐在仿“宫保第”的建筑内,让人感觉到风光重现的味道,然而也只
有“味道”而已,荣耀环绕的西关邓华熙府第,早已在岁月中飘零而去。
家族大视野
当代文化危机,呈现为家庭危机
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家”是一个温暖的字眼。家庭是中国人情感运作的第一界面,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枢纽地带,是决定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唯一尺度。从宗族家庭、父系家庭到夫妻家庭的历史演变中,有关“家”的核心价值,是在人们的情感体验中得到确认的。这些核心价值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归宿感、准宗教情绪、安全感、充实感相关,并以家庭生活的实际效果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否快乐,是否健康。当一个人处于极端糟糕的境地时,人们会形容他“如丧家之犬”;“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诅咒;国家意识的具体落点依然是“家”,所以才有了“国”与“家”的汉语联合词组,而英文中的“NATION”与族群相关,“COUNTRY”则与地理意义相关,汉语中的“国”则与“家”相关。
正是“家”凝聚了中国人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所谓价值共同体,其内核就是“家”。儒家文化的天、地、君、亲、师,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同时还是内在的精神结构,其中各项的矛盾对立与转换并置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政治观和伦理观。因此,家庭场域的私人性并不突出,个人是婚姻关系的产物,婚姻关系受制于宗族原则,而宗族则成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物(尤其宋明儒学得到推广之后)。个人就像水融入水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二元的,反而是同构的、蔓延的、网络状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恰恰是极其活跃的家庭生活,使得女人的身影像幽灵一样,游走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对男人的要求其实更为严苛。在历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其主要的言说对象是男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实际上是把女人放在了“君子道德”的对立面,就是说传统文化并没有要求女人去做“君子”,严格履行“礼”。这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定在“内闱”之中的女人,在家庭生活的内部,有了相对宽松的操作自由。女人游弋在文化内核的边缘区域,作为道德理想的总体化身——国家,对男人的个体训诫步骤严密,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经典《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就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而女人是“齐家”这项道德事务的协助者,但实际上却成了主要的操作者——习语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
成为操作者,并不意味着在传统文化的架构中,女人的家庭地位就得到认可。因为在妻妾制度、父权中心、生育制度、婚嫁习俗以及性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女人的选择权受到限制。但从文化自身内部来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容易陷入迷宫式的话语陷阱中。并且作为历史书写的缺席者,我们听不到女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只知道这些女人是母亲、妻子、小妾、女仆、女儿、内室、家眷等等。
因此,没有经历过自发的妇女运动洗礼的中国女人,“家”被体验为某种文化舒适区,其舒适度源自有关“家”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小女孩的游戏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过家家”,“家”承载了女人的梦想、情感甚至权力意志,她们像守卫疆土的战士,维护着家庭的完整与稳定。成为“女主人”依然是现代女性的幸福尺度,在可以掌控着什么的幻觉中,或许是丈夫孩子?女人们耗尽了一生的智慧。但当代文化危机,其最隐秘深刻的部分,实际上呈现为现代人的家庭危机。个人与家的关系,家庭结构的内在变化,家庭功能的入不敷出,让传统的面目像一个熟人的诡计,与现代人的文化想象力及其困难处境,展开了一场人性内部的持久战争。 □ 张念
历史的枢纽
当年叱咤西关,而今只剩追忆
早上8时,81岁的邓圻同穿戴整齐,准时出现在陶陶居门口,坐定后叫上几碟点心,翻翻当天的报纸,或与一众诗人书友谈天说地。
喝早茶的习惯从他十几岁开始,保持了60多年。这位典型的西关少爷,一直不愿搬离西关,到天河区的儿子家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平日里,他在家看书写字,偶尔下楼闲步于西关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虽然青石板路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这里的一楼一草一木都深深印刻在他心里。
上个世纪初,西关一带曾经是豪门雅士聚集之地,那些庭院深深的青砖大屋,穿戴摩登的西关小姐,无不成为老广州心中的一道风景。
作为老广州经济和文化的命脉,西关有着掩不住的风情、说不完的故事。曾在历史留下深刻痕迹的人物在这里风云际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抓住了西关这条线,其实也等于抓住了广州近现代史的主要脉络之一。
邓氏家族只是西关无数参与到那段历史的名门望族的一个缩影。从后人保留的书信中便可看出端倪:康有为、梁启超、朱九江、李鸿章、翁同和、张之洞、黄公度、陈述叔、黄节,乃至光绪皇帝,无数响亮的名字都曾与邓家有过这样那样的交集。
正是一批像邓华熙这样的开明士绅的推动下,广东孕育出了无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使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几经风雨,散落在西关一带的大户人家均已烟消云散、难觅痕迹。房屋被拆,后人多散落海外,仍然坚守在西关的恐怕不多了,邓圻同算是一个。为什么80年来对这里不离不弃?他饱含深情地朗诵起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后代访谈
讲述人:邓圻同,1926年生,邓华熙之幼孙,邓又同之弟。出生时祖父邓华熙已去世十年,与其父邓本逵、其叔邓毓生、其兄邓又同长居于祖屋,目睹整个家族的变迁。广州沦陷后曾逃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只好与其母返回日本人统治下的广州,并从此一直居住在西关。
邓华熙曾向光绪帝两次推荐《盛世危言》
光绪二十年(1894),长5卷的《盛世危言》横空出世,全书30万字,不仅积极主张变法图强,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鼓吹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次年3月,光绪皇帝读后嘉叹不已,立即诏命印刷2000部,分发诸大臣阅读。
该书的作者就是我祖父邓华熙的广东老乡郑观应。时任江苏布政使的祖父读到这本著作后,感慨万分,曾先后两次将其推荐给光绪皇帝。他在《上光绪帝荐书》上这样评价此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
正是祖父与朝中众大臣的力荐,使得该书风靡全国上下。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
邓华熙曾创办武备学堂及银元局
光绪二十二年(1896)7月,古稀之年的祖父踏上老城安庆的江岸。自此开始,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作为安徽巡抚,以他力所能及的力量,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为安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发展,注入了世纪末的活力。
上任半年之后,祖父奏请筹办求是学堂,强调以西学造就“既通西学、又切时务”的人才。同一年,继张之洞湖北武备学堂后,祖父又在安庆创办安徽武备学堂,首批招收新生40人。中国近代史上不少有影响的人物,如张汇滔、倪映典、石德宽、冷御秋等,均毕业于这所学校。
也是在同一时期,祖父以“安徽省制钱缺少”为由,上递奏折,要求“铸造银元以便民用而维圜法”,获批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4月14日成立安徽银元局。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安徽银元局创办始末就有过非常生动详实的叙述。
2004年易趣网收藏品拍卖,一枚“二十三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银元最终以50万人民币天价成交,拍者是一位远在美国的买家,在收藏界引起强烈反响。这枚银元就是我祖父当时在安徽银元局使用的样币。后来我专门在家中查找了一番,希望找到当年铸造的银元,遍寻不获,又询问在香港的兄长,他也未曾见过,真是可惜。
孙中山任大元帅后曾专赴邓府拜访
思想开通的祖父在辛亥革命中也起过特殊作用。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在全国二十四个省中,有十个省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给广东革命形势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农历九月初,广东各地革命党人密集广州,而广州的满洲八旗士兵,因思“不战亦死,战或得生”,表示“坚决防守,死里挣扎”,广州局势非常紧张,战事一触即发。当时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举棋不定,本已辞官的祖父被重邀出山,与清朝名臣梁鼎芬主持咨议局会议。会议在西关下九路的农务总会开了两天,祖父提出“顺应潮流,拥护共和”,促使广东政权顺利移交革命政府。
孙中山1912年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后,还专程赴邓府拜访。当时他一行乘坐三顶轿子前来(广州未开辟马路),后面有两位卫兵。轿子在宫保第轿厅停下,他一身白色中山装,手持白色通帽。身穿长衫马褂的家父即上前向他作揖表示欢迎,被他紧握住双手。孙中山看见轿厅墙壁上端挂着几个红底金字的功名牌匾,分别为:赏给太子少保、赏给头品顶戴、钦点监察御史、署理漕运总督,注视良久。接着家父将他一行引进客厅,祖父已站在门前迎候。主宾坐下寒暄,自然谈起广东和平移交政权的事,孙中山对祖父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谢,并称祖父为“德高望重的开明士绅”,征求他对治粤的意见。祖父说:“务望孙先生和胡汉民都督造福乡梓,使广东长治久安。”
对孙中山的造访,祖父事前已专门做了一番准备。他听说孙中山爱吃西餐,当日下午6时左右,安排在花园餐厅以西餐款待客人,当时使用的餐具数件,均为银合金制造。抗日战争时,我们全家避难于香港,这批餐具连同其他财物已被贼人偷去,硕果仅存的几件,也于1996年捐献给了荔湾博物馆。
□ 地理记忆
旧时风光府第,已被“大卸八块”
邓华熙故居邓宫保第为典型的西关大屋,占地一千多平方,位居广州多宝路18号。1902年邓华熙退隐故里,坊众央其为街道命名,邓华熙便借“物华天宝”之意,题下“多宝大街”四字。自此,多宝大街、多宝南横、多宝坊、多宝街等街名,成为广州老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据邓家老人回忆,当年多宝街一带房屋多为邓家祖产,不少远房亲戚前来投靠,皆安顿于此,邓家后人靠收租度日。
1930年左右,大宅门家道中落,宫保第之三开间花园及其他建筑终于腾空,租给广州市立小学做校舍。1951年,邓家祖居被国家征用,历经改建,已不复当年模样。宫保第的后花园所在,现已改为多宝幼儿园,邓家的第四代、第五代曾回此地上学。而祖居其他部分均已改为侨光制药厂。
坐落于龙津西路和逢源北街的荔湾博物馆内,有一栋西关大屋式建筑,即参考邓宫保第的建筑结构修建,内里摆设亦重现了邓家当时的情景。翠竹掩映下的青砖大屋,时有粤曲南音从隔壁窗外飘过。
.jpg)
光绪赐给邓华熙的对联。
.jpg)
康有为写给邓华熙的求画诗。
.jpg)
“宫保第”的后花园所在,现已建了一家幼儿园。车水马龙的喧闹街道,再也寻不到当年的风景。
.jpg)
1902年邓华熙退隐故里,人们请他为街道命名,他便题下“多宝大
街”。从此,含“多宝”字样的路名,刻入广州城的文化记忆。
.jpg)
邓华熙画像。
.jpg)
邓又同夫妇。
.jpg)
邓圻同夫妇(后)及母亲、妹妹。
后世逸闻
邓又同大婚
老西关最后一场奢华婚礼
1937年农历二月廿六日,邓华熙之孙邓又同21岁,奉父母之命与陈燕环小姐以三书六礼的形式结婚。陈父为省港富商,住在西关宝源路。陈小姐当年21岁,毕业于西关务本学校,是朱雪公老师的学生。
这段婚姻的统筹办理工作,双方家长委托邓又同的同胞姐夫操办,他是西关首富岑弼西的第13个儿子,为人热诚,又乐于助人,特别喜欢热闹。
整个婚事仪式包括:在男方家中婚聘过大礼、迎娶、翌日媒妁、三朝回门、四朝至六朝宴岳父母等等;在女方家里则有从办嫁妆、订服装、妆奁游街送往男家等等,同时,还在六天之内,筵开几百席。整个婚事珠光宝气、锣鼓喧天、喜事盈门。为安全起见,还聘请一队十人组成的特警,在家的周围保护。
邓又同成婚的第二年(1938年),广州沦陷,全家迁往香港。于是这次婚嫁就成为历史上西关地区最后一次传统又隆重婚礼。
邓四小姐做演员
西关小姐中的电影明星
邓华熙次子邓毓生有六个女儿,其中第四个女儿叫纤霞小姐。她的容貌、肤色、仪态在所有姐妹中最为出色,从小聪颖过人,口齿伶俐,穿着出众。当年西关少爷、青年子弟追求者甚众。
邓四小姐紧跟时代,喜欢交际,崇尚自由,爱好艺术。当年广州电影事业先驱罗明佑,在西关逢源区设新民电影演业公司,公开征求演员。她为追求艺术,也想应征,但这违背了封建家庭的家规,因此她不敢告诉父母,只有先离家出走,在外居住,再去应征。
新民公司罗明佑见她才貌出众,就录取了她做演员。过了半年,新民电影公司创业电影爱情故事片《胭脂》在十八甫的一间新影院放映的广告,主角就是邓纤霞。新片上场,连续放映二十多天,大家都争相一睹她的芳姿,成为一时盛事。
但是那时她仍不敢回家,怕惹家里生气。一年过后,新民公司因资本关系,临时停业,四姐便应邀加入新开的钻石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开拍的第一部片,是爱情故事片《爱河潮》,还是她任主角。拍片两年后,她就离开了影艺圈。经过家里亲友斡旋劝说,家中长辈也不再责怪她。后来她认识了岭南大学的高才生吕惠君并与之结婚,她的丈夫后来成为中国驻印尼领事。
“赐书楼”珍贵藏品
后人陆续捐献千余遗宝
邓家后人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光绪赐给邓华熙的那副对联。上联是“淇水烟波半含春色”,下联为“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作者是乾隆的第十一子、被誉为清初四大书法名家之一的成亲王永瑆。大约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绪皇帝将此对联及数百种书籍一起派人送到了邓府。邓华熙视若珍宝,当即在府第附近兴建“赐书楼”,专门存放皇家赐予的书籍字画。邓家后人多在此楼中开始一生中文学艺术的启蒙教育。
多年来,邓氏后人均很珍爱祖父的名声,不断向政府和博物馆捐出祖上的藏品,至今已捐出1400多件宝物。
□ 族谱词典
邓华熙 曾任清朝封疆大吏
邓华熙(1826-1916),字小赤,又作小石,顺德龙山人,1851年恩科中举,1854年参与顺德团练局事务,因筹饷有功,议叙刑部员外郎。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任京师巡防处办事员,条陈抗敌方略数千言,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提拔为刑部郎中。此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云南大理府知府、湖北布政使、江苏布政使等职。1896-1902年,先后任安徽、山西、贵州巡抚。1903年因病辞官回原籍,还乡后以书画养性,书宗二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与梁鼎芬(清名臣)主持咨议局会议,宣布广东独立。1916年病逝于广州,卒年九十岁,谥“和简”。
邓本逵 以白话文发禁烟告示
邓本逵(1861-1936),华熙公长子,原名本仪,字用甫,亦擅书。于清末时任浙江省宁波绍兴道台,任内力主禁烟,提出禁烟应先禁种,以断绝其来源,曾以白话文发出禁烟告示,使妇孺皆懂。武昌起义后,邓本逵和平移交政权,百姓夹道欢送,咸称“贤良太守”。民国后曾任职于广东航运局,退休后以诗书自娱,1937年在广州西关祖居病逝。
邓毓生 “广东坟山公所所长”
邓毓生(生卒年月不详),华熙公次子,信奉风水。1916年华熙公去世后,一直为寻找葬父墓地奔波,以至广州近郊人氏及“山中”(介绍买墓地者)无人不知其为父觅地劳碌,后被推举为“广东坟山公所所长”。1933年,于远郊寻找山坟时为贼人所掳,后托人辗转赎回。后一年在广州白云山下锦衣岭总算找到墓地,便将棺椁移葬。从停柩于福如山庄到入土为安,为时长达十八年,花费达数万银元。
邓又同 曾去印度拜见甘地
邓又同(1916-2003),邓华熙之玄孙,邓本逵之哲嗣。少岁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法科,曾游学四方,在印度拜见了甘地,在国际大学拜见了诗人泰戈尔,曾乘邮轮漂洋过海,去到西欧。后历任省、港、澳各中学校长,从事文化事业50余年,在港从事编纂工作,并常年供职于民间学术机构学海书楼。
□ 专家视角
后人捐赠文物“义举”值得钦佩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邱捷
邓华熙作为晚清时期的高官,晚年回乡后,对广东的慈善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他的后人将家族的一批珍贵文物很好地保存下来,并先后无偿地将上千件捐献给了国家,很了不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对其后人的义举非常钦佩。
□ 坊间一语
一次在一古玩市场淘到的一本《历朝闺雅》,初看便觉该书朱痕累累,仔细辨认藏书印,发现其中一枚属于光绪年间三省巡抚、广东籍大官邓华熙。邓华熙还在书中补写了一段淘书小故事,讲述了该书的渊源是来自宫廷,更是皇帝所赐之书,他在“琉璃厂乱书堆”中淘到时,“如获异宝”。藏书之人自然心有灵犀,我当即买下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本书上还有邓华熙儿子、孙子的藏书印,遂萌生了探访其故居的念头。2005年我专门赴广州,在西关一带寻访邓华熙故居,竟然听闻其孙邓圻同仍健在,可惜没有机会见上一面。
——深圳藏书爱好者 邹毅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索娃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邹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