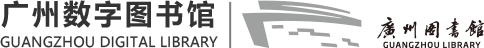2017年12月17日下午,刘斯翰先生诗词系列讲座第45讲广州人文馆中堂交流区举行,刘斯翰老师继续开讲秦观词,赏析了《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点绛唇(醉漾轻舟)》 两首词。

刘斯翰先生诗词系列讲座第45讲开讲
水龙吟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gǔ)雕鞍骤。
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zhòu)。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注:
连远,当以“连苑”为是。 小楼连苑,张籍《节妇吟》:“妾家高楼连苑起”。
词作点评:
对这首词开头二句,东坡有个批评。南宋人曾慥《高斋诗话》记载:
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
东坡的批评自有他的道理。不过,却也不能作为定论。因为写作习惯,往往和作者个人的审美趣味相关联,尤其是象秦观这样的大家的成功之作,更不能随随便便就听信了东坡的一句话,我们还应当从整体去考察一下。如果换个角度去看,我们会发现,这首词的风格总体而言是轻浅明白的。惟有开头二句和下片开头一句,流露出雕琢的形迹,且来看看这两句: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
《全宋词》本取作“连远”,我更认同“连苑”的版本,有两个原因:
一、“连苑”有出处,属于用典,暗示了女子身份(张籍原诗用以描写女子是贵夫人,这里则转为描写青楼女子),而“连远”既无出处,也用得并不妥贴,“连远横空”,更象是高塔之类,而不合小楼;
二、“连苑”既符合青楼的形势,与“绣毂雕鞍骤”相结合,一幅《青楼游乐图》便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而“连远”则无此气氛。还可再加剖析: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或暗用典,或明用修饰,形成一种刻意追求丽密(颇近花间体)的审美意趣,其间以“连、横、下窥、骤”等动词贯串,打破可能造成的堆砌、呆板,其用心可谓良苦。
这样处理,目的是留住读者的注意力,不使一眼滑过,而放在开头,尤其显得出手不凡。这样看来,东坡只是挑剔它有词费的毛病,却未考虑秦观以这样的开头,著意在它的审美效果,而不在交代“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
通过这开头两句,我们已经很清晰地了解,词家描述的是青楼之事。于是他接下来笔锋一转,把读者带入美好的春天里:
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这是一幅晚春的风景,我们随口一念,立即就被那有如行云流水的句子,带进了令人不由自主受到感染的唯美情境之中。这正是秦观词的看家本领,它从柳永悟入,又化为自己独有的迷人词境。前人评“少游词如花初胎”(周济),确能道出其审美志趣,在于既是天生丽质,自然要眇,又与词体轻柔婉媚的特点拍合无间。不过,虽然这看似信笔一挥而就,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会发现此中描写的技巧运用其实是很讲究的,沁透了词家的才思。
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节来看:
首先,“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是一节,前两句用对仗,乍看时却不觉察,这是由于词家有意避开简单的骈偶。他以“朱帘”对“单衣”,前者强调了颜色(视觉),后者突出了质地(触感);又以“半卷”对“初试”,前者是客观状态,后者是主观行为,字面虽对,内容则错开,这处理粗看不易觉察,要细加剖析才能领会,尤其下笔之轻(这一点周济也已经指出)十分难得,是秦氏的天生禀赋使然。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是第二节,这里也是前面对仗,不过下字十分讲究:风是轻的,有点儿微冷,把春末夏初显露的温暖点“破”了,一个“破”字就亏他想得出来!天已放晴,但雨水不甘心就此打住,它仍在似有似无游荡,一个“弄”字十分精准传神。下笔仍然很轻,是词家有意营造的审美境界。炼字乃是诗人的个性之所在,这在秦观笔下尤其明显。
第三节:“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相比而言,前面两节更着重从主观方面下笔,即词家对周遭环境的感受,而这一节,则拓展开去,节奏由静趋动,由微婉而转为奔放。你听,先是挑花担叫卖的么喝声,一拨去了又一拨来(这也正是青楼的生态景观之一),等到他们逐渐远去,直至叫卖声完全消失。院落便安静下来,这会儿雨也停了,太阳已经偏西,淡淡的阳光笼罩着黄昏,一阵晚风吹起,把纷纷扬扬的柳絮吹成阵阵红尘,把它们一直吹到鸳鸯瓦上去……这里用“红”字形容斜阳中的柳絮,很值得称赏。
柳絮本白,染上暮色化为暗红,虽然现实看来未必如此,却不妨碍词家回忆中的印象。如果一定要完全写实,效果反不如它优美,况且读者由此还可想象到春末的落英缤纷,那又非“红”字不能替代。这里,我们不妨拿张先咏柳絮的名句来比较一下,真可谓各擅胜场:
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这一节除却卖花,秦观并没有对青楼生活作更多描述,而专力描写暮春黄昏的美景,作为两情相悦的映衬。这也是秦词取雅避俗的一法。
下片开头的起句,点出上片是旧事回忆。“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玉佩,读书人的象征。《礼记》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李商隐诗有“鲍壶冰皎洁,王佩玉丁东。”的句子(鲍照《代白头吟》:“清如玉壶冰”。挚虞《决录要注》:“汉末绝无玉佩。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此句用典(商隐成句),掺入了雕琢的意趣,其用意我们后面再说。“参差难又”,是说别后虽曾一再相约,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重聚。“名韁利锁”,是说自己一直在为科考奔走,注意,这也是柳永词中的成句(《夏云峰》:“向此免、名韁利锁,虚费光阴”)。
前边引曾氏《高斋诗话》,说这词是秦观写赠蔡州官妓的,我看不对,据年表,秦观曾在蔡州任职,但之后并未再到会稽。秦观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则是尚未中举时的事。所以曾氏记载其实自相矛盾,不足取信。况且,硬说秦观把官妓名字镶嵌进词中,也实在令人莫名其妙。所以,我认为此词无论写当下还是回忆往事,秦的身份都还是白衣。
“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则是变用了李贺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它本来就是描写别离的名句,秦观的本领,是取其精华,转换为词的句子,而做得自然熨帖,丝毫不见勉强的痕迹。知道它的出处,会为之叹服,不知道它的出处,也会为这妙喻的抒情留下深刻印象。
词的主题至此已大致完成,余下的篇幅,只是对抒情和回忆进行反复勾勒: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是回应开头,作进一步勾勒,并以“不堪回首”为前面的抒情增加份量。句式采用对仗,与上片两个对仗句呼应,旋律也稍作重现。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当时皓月,四字吃紧。当时,分指上片之旧情,与此际之今情。皓月,即明月,也可以理解为是月圆之夜,这既是月圆而人不圆的暗示,又点出当日在月圆之夜两人的欢聚,当时如彼美满,今夜如此失意!“向人依旧”寄托了无限相思,和无限怅惘。明明是人多情,却说是明月多情。明明是说自己情怀未变,却要说是明月依旧。美学上有所谓“移情”之说,秦观当不知道这个理论,却以他的创造力作了成功的实践。
最后,我们把这词整体浏览一遍,会发现上片开头的雕琢和下片首句的用典,与其余部分明快轻清的风格,形成一种反拨,一种对峙,倘若尝试把这雕琢的句子换成与其他风格一致,我们会感觉到,在它的节奏上不免太过浮浅轻盈,而缺乏变化的顿挫和力度。在我看来,这两处其实相当于使用了“重笔”,它令人要停下来理解、思索,而不能轻轻放过。如果秦观词只是一味轻浅,就不可能有如此之高的审美地位了。

刘斯翰老师深入浅出鉴赏秦观词
点绛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
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
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词作点评:
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时有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采药迷路,误入桃源洞,遇仙女结为夫妇的故事。以后在诗人笔下演变为男女欢会之所的代词。唐诗人刘长卿有《过白鹤观寻岑秀才不遇》诗,即引其事:“不知方外客,何事锁空房。应向桃源里,教他唤阮郎。”而南唐冯延巳《点绛唇》亦用之作词云:
荫绿围红,梦琼家在桃源住。画桥当路,临水开朱户。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
秦观这首词,或者便是受冯氏的触发而作。如果真是这样,在词家心里,抱有与之一较高下的心态,则是很可能的。有意思的是,两相比较,冯词显得直白明快,而秦词则要含蓄许多。
首先,秦观有意把两个桃源典故掺和起来。即除了刘义庆的故事,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们既可以把它看做写恋情,又可以把它视作《桃花源记》的词体概括。或者说,它乍看时是咏渔人偶然闯入避世桃源的故事,侧起脑袋想想,才确定其实是借刘阮桃源遇仙写词人的一段风情。这比冯词就够含蓄的了。
再看看他具体又是怎么写的吧!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上片四句,好象一气就把《桃花源记》打包了。也可以说把“刘阮遇仙”的故事概打包了。而且还那么举止潇洒,身段优雅。真个是举重若轻啊!这还不止,你看,前二句更象是陶渊明的桃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隔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而后二句更象是刘、阮的桃源:
至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但是,那个“醉”字,却泄漏了词家主体——这是刘阮采药、渔夫捕鱼都不会有的。我们只要改变一下,知道“桃源”在此不过是青楼的代称,则立即进入词家用典故掩蔽的真相——上片不过说自己偶然来到某处青楼,遇上一位女子,两情相悦,可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得不离开。
我们知道,上片用的是过去时,下片才是现在时: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此日,词家旧地重来,发现物是人非——伊人已再也找不到了。词中用“不记来时路”,含蓄地表述,仍然保持着上片使用“桃源”典故的方式,不加点破。但采用不惜篇幅地景物描写,来寄寓他的失望和怅惘之情。这样的描写,是两个“桃源”故事都没有的,因为它们属于词家主体的所想,所见,所感。这段风景描写,与上片的叙事互相映衬,令全词显得充实、饱满。其中,用“乱红如雨”描画出,独具秦词特色的凄美境界,尤其怆人心目,也是全词最出彩之笔。
我们说过,“旧地重来,往事如烟”的主题,是宋词的重要抒情主题之一,其中佳作名篇,层出不穷。今天的人们,对此也许不再如古人那样牵情伤怀。现代流行曲中,这样的主题并不特出。我想,这是因为现代人们分离以后,还有许多工具,可以克服时空的障碍。不象古人,男女之间一旦分离,常常就意味着此生不再得见,生离与死别是差不多的。

词友用方言朗诵《水龙吟(小楼连远横空)》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本期讲座吸引了60多位读者参加,词友们意犹未尽,与刘斯翰老师继续交流。许多读者纷纷预约报名下一讲,讲座得到广大诗词爱好者的肯定与好评。

课后交流
[下期预告]
第四十六讲:秦观词选讲(五)
千秋岁(水边沙外)
踏莎行(雾失楼台)
时间:2018年1月14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广州图书馆北9楼广州人文馆
更多活动信息敬请关注广州人文馆新浪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