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鉴定
产品名称:南方的另类音乐
代表产品:王磊
质量鉴定:广州摇滚是潮湿的、自由的、与时俱进的,更是包容的。王磊是这块热土生长出的摇滚大树。他和音乐公社与《南方大摇滚》一起,指出了中国摇滚的另一种可能——一条人性化的道路。
质检报告
少点愤怒,多点自由
广州的摇滚是潮湿的。与天气有关,也与广州摇滚人的心态有关。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摇滚的宏大叙事和高蹈偏激不同,以广州为代表的南方摇滚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不是生活的敌人,而是一根对抗盲目的针。他们对生活发言,而不是空洞地诅咒和宣泄。比起北京摇滚的“权力话语”,广州摇滚更加人性,更加真实,更加自由。
广州的摇滚是“与时俱进”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新的资讯意味着新的可能。作为“打口文化”的前沿,它不但把最新式的“武器”递到摇滚人手中,同时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高素质的听众。王磊是一个典型,摇滚、民谣、舞曲、实验电子和民族音乐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并且融会贯通。
无数的乐评人众口一词“王磊是个天才”。他身上集中了广州的潮湿和四川的麻辣之间的冲突。他的存在也集中体现了广州的包容。和所谓中心的距离,强烈的孤独感,对生活的爱和恨,成就了他,也旗帜鲜明地显示了摇滚的另一种可能。南方摇滚,旗帜飘飘。
那些疑惑广州有没有摇滚的人,只是习惯了以唯一的标准来判断摇滚。正如广州代表了未来市民、社会的前途,诞生于这块潮湿、温暖、班驳土地上的摇滚更加显示了我们这个商业时代心灵的渴求和本能的呼唤。
全息广州
摇滚或石狮子
10年前有位诗人自豪地向我宣称:广州诗歌在全国可以排在第四。我的回答是:广州的足球在全国还排在第二呢(那年太阳神拿了全国亚军)!法国有记者采访王磊:“你认为中国的摇滚乐以后会超过美国吗?”如果是我,我会反问:“你认为中国足球队今后会拿世界冠军吗?”
将艺术等同于体育比赛,以地域乃至民族的文化幻觉去取代艺术现实,这是在讨论诸如“广州摇滚”乃至“中国摇滚”之类问题之前首先要避免的。没有什么“南北摇滚擂台赛”,也没有什么“国际音乐之都”的合格证等着你去申请。音乐不是意识形态,摇滚也不是农民起义。假如非要论证“广州摇滚”,也只能说:它从前穿着开裆裤,现在是青春期梦遗,但还没有像胡子一样天天疯长、像过街老鼠一样肆无忌惮。
广州,一个热气腾腾的市民社会,潮湿、混乱,始终是现实主义生动活泼的艺术资源,然而又被开发得远远不够。这座城市不鼓励文化自大狂——至多滋生红包艺术家——更有利于培养独立精神。王磊是一个游放于北京摇滚权力体系之外的最佳例证,游离于摇滚、电子舞曲体系之外的先锋钟敏杰是又一个例证。
广州是打口文化发源地,乐迷素质明显高于创作实力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放的商业市场以及相对敏锐的传媒之间,摇滚及新生音乐文化在广州仍有越来越大的空间。Livehome 3这一音乐现场策划团队的产生,以及法国国际音乐节、新年摇滚音乐节的举办,使2003年成为广州音乐文化的转折点。
但广州摇滚还远没有找到自己鲜明有力的表达方式——即便在主流摇滚系统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像上海那样出现一个多少有别于北京的前卫摇滚群落以及脱离摇滚体系的实验电子群落。假如哪天提到“广州摇滚”再不用言必称王磊,甚至不用言必称摇滚,那才真正说明“广州摇滚”的进步,以至于“广州摇滚”这一标签本身也已失去意义。
你有没留意过广州的石狮子和别处不一样?——都雕上一根粗壮的阳具!如果你愿意,可以将之视为“广州摇滚”的象征。
何止摇滚,谁说广州不好玩不性感?
□张晓舟
■追忆年华
我和广州的地下音乐圈
我所见到的广州地下音乐圈算起来正好将近十年。十年中,一批人出现,另一批人消失;大部分的人都成了不错的朋友,而有的人却成了敌人,不过谁也没有成为英雄。
我正巧是一个从来记不住年月日的人,所以一直没有把旧事翻出来的打算。只是在去年年底的某日于深圳,一位摇滚青年盯着我说:“你好像很面熟,你是……”“曾向华。”他说了一句也许我终身难忘的话:“老前辈了!”在不知该觉得荣幸还是尴尬之余,我突然自觉可以鼓起勇气来写一写印象中的我和广州的地下音乐圈。
牛扒城的民歌手
在这里要首先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地下”二字对于广州的这种情况很合用,它只是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时的一个替代语。
广州比较早期的地下音乐人们聚到一起,常会为这样一件事而觉得奇怪: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西部牛仔啤酒牛扒城这间酒廊当过弹唱歌手。这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的地下音乐是从民谣开始的。我也是其中最早的那批民歌手之一。在这里,我见到了王闻、原“SHADOWS”乐队的灵魂人物林羽、方辉、我原来学校乐队的吉他手李宗贤、鼓手陈郁葱及后来去了北京的杨一等人。45分钟的演出时间,三四十元一场的演出费;这已足以使1991年初广州的民歌手们趋之若鹜了。
赚钱有术的台湾老板、昏暗的灯光下特别的装修、客人进门时侍应生高呼的“欢迎光临”、奇差的音响效果和民歌手,形成了牛扒城独特的吸引力。这里渐渐聚集了一批又一批文人、雅士和酒疯子;我们有时与来捧场的朋友们把酒欢歌、调情悦趣,有时与撒酒疯的客人拍桌子骂娘、大打出手。在酒杯的碰撞声中音乐只是赚钱、练嗓子的手段,并无情趣可言,这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林羽拉上来跟他唱二声部。
音乐公社的开始与结束
一天我在公司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我当时不认识的钟名。他是个非常礼貌的人,当他告诉我现在有一群朋友想组织一个地下音乐人团体,并很客气地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时,我在很客气地表示愿意的同时,内心却已激动得不行——这个想法太好了!
音乐公社的成立标志着广州地下音乐第一个高潮的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艳阳天、KSM、NO NAME、铁蜘蛛、支点、藻泽、一窝蜂、焦距、王闻、田敏、朱昕荣和我等(还有一些我记不起来的但未必不重要的)乐队和个人突然频繁地出现在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上,为数不多的几次“社员汇演”为“社员”同志们提供了交流、观摩的机会,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公社的存在。
音乐公社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广州地下音乐大规模地曝光,这也使专业音乐人、音像公司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市场;1994年年中,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南方大摇滚(一)”的录制完成,在标志着音乐公社的成功的同时也意味着音乐公社的结束。
曾向华(广州早期摇滚人)
王磊:迷乱城市里的孤独斗士
王磊在1998年“以音乐的名义”音乐节上表演。 曾翰 摄
在广州摇滚音乐中,最特别的是王磊现象。他对广州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既爱又恨。广州的潮湿、抑郁,和四川的麻辣之间的冲突,所以有了像《石牌村》这样的作品。本质上王磊是在逃避类似于北京这样的权力体系。广州的自由、包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相对于北京来说他是另类。他始终和北京中心保持一种距离。
王磊是个天才,他的成绩似乎和时间地域没有关系。但是却正是在广州这座混乱焦躁的城市里,有了一个孤独的王磊,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独造就了他独特的摇滚。没有谁能够否认一个城市对于个体的影响。对于音乐创作来说,没有生活就意味着没有音乐。没有广州也就很难想像是否有这样一个王磊。
王磊说他自己是反摇滚的。其实这并不完全正确,作为一种音乐,本来就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式。王磊的音乐或许不是纯粹的摇滚,他只代表南方,代表一种自由,淡化了功利。因为在广州你不可能有太多的喝彩,不容易产生一种害人的文化幻觉。这是王磊作为个体和广州这座城市最本质的联系。
■随想录
抛弃虚妄,呼唤本能
广州有没有摇滚?本地人带着疑惑,“中心人”带着讥诮。我要说,有。但这不是那种你熟悉得可以当做按摩和迷幻药的摇滚,不是让你简单地获得愤世嫉俗的自慰的摇滚,也不是让你从受虐中获得快感的摇滚。它不是把你带往理想主义的天堂和悲观主义的深渊,而是让你充满了人间的爱与恨,温暖和疼痛,听到血液淙淙流响。
广州需要不需要摇滚?大腹便便的老人和志得意满的中年人提出疑问。摇滚是什么?是青春,是力量,是愤怒,是不安于现状。当我们在灯红酒绿中看到城市因失血而苍白的面容,除了呐喊和痛哭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找回自己?在备受赞美的商品社会和庸常生活里,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节奏下,在生存的压力像影子一样跟随下,在穷人和富人显露出血淋淋的鸿沟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摇滚。如果你不甘心盲目、蜕化、冷漠。摇滚让你在水泥森林中一次次复活。
摇滚当然是一种姿态,但可悲的是它已经被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们简化成一种唯一的姿态。它的面目如此僵硬,宛如行尸走肉。也许在潮湿的南方,它会重新生长出血液,迸发出真实、坚决、热烈的呐喊。
■群英谱
盲流
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解散后主唱黄勃现在北京组建了Omen乐队,吉他手易云钢在上海弹爵士。
焦炬
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外语学院乐队,主唱宋晓军后来独自发展,贝斯手郭劲刚现在是著名录音师兼制作人,他制作了木马、废墟的专辑,也是迷笛音乐节、广州新年摇滚音乐节的调音师。
雨中猴群
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广州外语学院乐队,风格在迷幻与朋克之间。
沼泽
沼泽乐队在雪山音乐节上的一跃。 曾翰 摄
从开平转战到广州的摇滚乐队。如今,沼泽乐队靠策划晚会、出租、搬运音响设备维持乐队的音乐创作。沼泽在广州这个独立音乐生存空间日益恶劣的环境下自资出版了同名专辑《沼泽》、EP《惊惶》和《求医记》。
吹波糖
“老乐队”吹波糖。 曾翰 摄
吹波糖乐队在广州成立多年,乐队成员都还年轻,很低调,音乐风格笼统地说是重型英伦。
无了期
无了期乐队始创于1999年秋,2003年出版了专辑《游戏》。
CO2
重金属的CO2乐队。 曾翰 摄
CO2(CARBONDIOXIDE)于1999年年中组队。主要风格是重金属,带有死亡金属的气质。
铜镜
中山大学的校园乐队,由5名在校学生组成,成立已三年,有10多首成熟作品,被视为广州摇滚最具潜力的乐队。
与非门
准确地说他们的音乐不是摇滚,他们以新鲜的流行电子曲风开始进入主流音乐市场。已出版两张专辑。
■关键词
乐评人
广州摇滚还有一笔非常丰厚的财富就是摇滚乐评人。他们不但是广州摇滚的权威见证者和积极鼓吹者,更对中国摇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晓舟、邱大立都是乐迷们耳熟能详、心悦诚服的名字。他们是新音乐形式的倡导者和广州经验的提炼总结者。在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摇滚之外,广州能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他们功勋卓著。
打口
作为海岸的省会城市,广州毗邻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打口带的前沿阵地。它带来了国外和港台最新的音乐资讯,不断地给广州摇滚最新武装,使得广州的摇滚乐在整体上更倾向英伦。可以说,广州摇滚乐的发生和成长以及特质的形成都与打口文化息息相关。
根据地
以前的一九九吧。 柴春芽 摄
现在的SOLO吧。 柴春芽 摄
下期预告
1987年,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三人成立了“新空气”组合。他们面对的是港台歌曲的一统天下。在这种“外来文化”的重重包围中,他们开拓了一条祖国大陆流行音乐的路。
专题执行/本报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廖文芳(署名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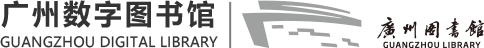


.gif)
.gif)
.gif)
.gif)
.gif)
.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