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决定丢下所有的资料,重新认识那条已经陈旧的报馆街,重新领悟那一代报人的情趣所在。老报,虽然岁月久远,然而毕竟符合当时民众的审美观念,小道消息不可缺少,大道理也同时存在,市场化的操作成熟到了极点。《宫帷艳史》、《打番鬼(洋人)》之类的栏目扣人心弦,勿论格调之高低,单单说市民愿意接受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现代文学。有人评论广州一向有小市民的作风,广州的原住民更是把实实在在进行到底,没有花哨的修饰,从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一种迎合的姿态,放下架子的民办报纸之所以能受宠,正是因为它没有脱离自己的读者。报馆街就在居民的身旁,每天经过都能够亲眼看到老编老记在里头刻版、撰稿的情形,“新闻纸”从来就不是“神话”,它就在普通市民的眼皮底下匆忙付印。从前的新闻与今日的新闻相比,同样地道、亲民,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变的只是报馆的形式,成了高楼大厦,成了城市的笔录。曲高和寡只能永远把自己打扮成臭肉朱门。
一路走下去,臆想当时的报人如何把凡尘生活与紧张时政记录下来,然后用这种精神把耳濡目染的情景按原样拷贝,继续走真实的道路。
地理记忆
繁华一场春梦
纵观广州近代报业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清末的萌芽期、民国及抗战期间的繁荣期、解放初期的重组期以及近年的高速发展期。其中前两个重要的阶段,标志着广州报业的诞生以及迅速膨胀,而在此期间出现的众多报馆,约有半数建于西关,其中包括广东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文日报《述报》、广东最早出版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广东群报》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来,西关具有广州近代报业最纯正的血统,若论地位则应赋予“发源地”之名了。西关报馆不但设立早,而且数量多:光绪、宣统年间,共有约70份报刊在穗创办发行,其中报馆地址可证实在西关的有30多家;民国初期,设馆西关的报业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第七甫、第八甫、十八甫等地,当时西关的报社有130多家,占当时广州报业的半数以上。
当年:从十八甫到光复中路
既然焦点集中在西关,追寻广州老报馆的遗迹便有了线索。民国时期广州的报馆多设立在第七甫、第八甫,这是一段首尾相接南北走向的老街,1931年,当时的市政府把第三甫至第八甫以及打铜街由北至南改建成大马路,并更名为“光复路”。
光复中路的门牌几经改变,记者经过多方寻访,终于找到这间据称是以前《环球报》所在的旧址
“光复”含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光复河山之意,修建成路之后,路面宽约12米,沿途多为民宅。原来的第七甫和第八甫老街也便在这个时候更名为“光复中路”。解放以前报馆最为密集的光复中路后来被民间称为“报纸街”或“报馆街”,这条街就是近代广州报业繁盛至极的缩影。
今日:历史印迹渺不可寻
如今的光复中路,已经完全没有昔日报馆林立的模样,号称12米宽的“大马路”,在现代城市宽敞大道的荫庇之下成了羊肠小道,古屋老街的情态风烛残年。沿途概览,还能找到些许老旧印刷厂以及货仓的影子,至于叱咤一时的众多报馆,随着年轻商铺的不断更新,如老酒换新瓶一般,纵使建筑没有过多的拆建更新,门面却是几经易手,难以辨认往日的痕迹了。
光复中路上一间小小的印刷厂,上了岁数的老人在产品包装上封装招贴这可能是和报馆街联系最密切的行业了。
工人们正在拆迁光复中路上的旧建筑,身后是现代化的高楼。也许过不了多久,所有的遗迹都将荡然无存。
稍微有点擦边的,便是在光复中路找到一间小小的印刷厂,上了岁数的老人辛勤劳作,在产品包装上封装招贴。无法想像当年印数过万的本地中文报章便是从这样的小房子里成叠送出,昔日广州报馆那种常见的以黑底大字报吸引行人目光的户外广告形式更已湮没在如今民舍及商铺的粉饰之中。荔湾区房产局的原局长潘老先生说,前两年还能在这里找到《环球报》等老报馆的痕迹,然而如今的广州城三月一小变,报馆非文物保护之列,转眼间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翻开解放前的《广州大观》,还有当时报馆地址的详细记录:《越华报》在光复中路114号、《环球报》在100号、《国华报》在76号、《现象报》在44号……还有《广东日报》、《前锋日报》、《建国日报》等等,再加上没有登记的其他小报,为数众多,昌盛之势可想而知。
掌故丛谈
架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老派的报馆,规模并不臃肿庞大,30人的采编队伍已属“浩大”,记者虽然不多,但也有高低级别之分。报社的主编每曰必有社评一章,针砭时弊、观点鲜明,功力自然在众人之上。
.jpg)
记者和编辑在解放以前属于“高薪一族”,这是一间他们经常光顾的茶楼旧址。
文艺界的名家则充当报界先锋,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评论都是由名家亲自操刀。工作最为简单的便是跑社区新闻的记者,当时的新闻采访工作相当“简捷”,记者只需到街区各处的警察分局守候及查阅每日的案件记录便能得到新闻线索。至于撰文,也一并按照案件记录的格式,语言简洁只求题材能够哗众取宠。所以当时跑社区新闻的记者级别最低,其工作也只限于每日与主管抄写的“分局事务”(警察局的公务员)喝茶、打麻将等等,以套取第一手新闻,西关一带的“分局”和茶楼成了新闻记者的常驻之所。另外还有一种“特约记者”,并不隶属于某家报馆,只以个人身份采写文章,特约记者其实多是有党派干系的“线人”,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政府部门甚至是高官府邸.并非普通记者可相比。
题材 风格多样天马行空
官报的格调比较正统,不荀言笑,以时政信息为主线,难以成为市民的饭后谈资,所以销售业绩不见得高不可攀。民报则不同,时常报道诸如街头斗殴、盗窃案件以及民政事务等琐碎小事,但却为大众所关注,另外再加上副刊幽默有趣、风格多样的文学小品以及天马行空的武林小说,更是符合读者的娱乐需求。要知道,当时的广州城娱乐项目并不多,大不了便是看看剧团表演之类的活动,大多数人家连收音机都买不起,所以几分钱一份报纸便成了主要的娱乐渠道了。
待遇 社会中坚高薪一族
记者和编辑在解放以前属于“高薪一族”,货币稳定的时候,编辑的工钱是每月20元,当时一角钱可以买到一打鸡蛋,所以这样的薪水已经大大超越社会平均工资了。至于记者的稿酬,一般是每篇六角、八角、一元三个等次,虽然老报纸的版面不多,但新闻工作的从业人员数目也很少,所以记者每月的薪金也很有保证,有“白领”的地位。记者中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状况,有些记者专挖政府部门和大公司的丑闻,并趁机索取财物,为人所不齿。
广告 顾客盈门财源滚滚
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只要言论实在,就能获得大量广告。解放以前广州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杂志,昕以许多大公司都会固定在报章上预定广告版位,那个时候的报纸虽然只有一页四版或顶多是两页纸而已,但广告的篇幅则占据1/4强,销售量大的报纸甚至有1/2是广告内容,广告市场的垄断造成了本地报纸如春笋般涌现的状况,直到抗战结束,这样大比例的广告篇幅才有所消减。大多数报纸都是自办发行,销量在三千份以上的报馆便可以维持经营。
报界先驱
报人也是闻人
陈荆鸿
曾历任《越华报》、《循环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早年受业于温肃、温幼菊,16岁赴上海,遂与黄宾虹、吴昌硕等结为忘年交,与康有为亦师亦友,有“岭南才子”之称。陈荆鸡20岁便与赵少昂、黄少强在各地开书画展,三人被誉为“岭南三子”。
南海十三郎
成名于香港的粤剧界名人,每有自认为得意的剧评或曲本一类作品,就投寄羊城三大报纸之一的《越华报》发表,并与当年兼为《越华报》副刊撰稿的名编剧家梁金堂订为文字之交。
席泽宗
中国科学院院士,早年曾经在广州多个报章上发表过学术文章,有《日食观测简史》(《建国日报》)、《中秋赏月》(《联合报》)等等。
这些学界的名人,是广州报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分子,他们发表过的作品代表着广州文化界的最高水平,由此也可看出广州的报纸并非一式的官样或小市民格调。
报林逸事
上夜班,饮早茶
新闻工作者一定要遇到上夜班的情况,就连副刊编辑也不可避免。一旦有重大新闻便全员出动,出“号外”、“增刊”,所有的编辑记者都要动员起来。有趣的是编辑记者下班之后要去喝早茶,居然也有等次之分——由于报馆集中在光复中路一带,所以不同报社的采编会聚集在一起喝“天光茶”。凌晨四点钟左右下班,各个报社的高级编辑、记者会到状元坊对面的“太如楼”聚会,远一点的便去“天元楼”;收入稍低的会到新大新公司的“国泰”;而组版的工人则习惯在北面的乐善戏院附近吃“大排档”。
复活历史
官报与民报
解放以前的广州报纸,大致可以分成官报、民报两大类,其中民报又可以分为半官半民以及小报两类。所谓官报,就是代表当时政府发言的官方报纸,比较出名的有《民国日报》,这份报纸后来被更名为《中山日报》,有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含义——中山先生的“总统就职宣言”便是最先在《民国日报》刊发。官报在当时多是进步报纸,但后期也出现了反动宣传的苗头。正派的理论包括北伐意义的推广、国共合作的言论支持等等,在思想领域方面较易为进步人士所接受,同时也成了当时的豪绅官僚了解现状、推断形势的信息来源,读者面比较狭窄,日发行量在五千份以下,有政府补贴作后盾。
民办的报纸则是以大众的喜好为根本,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比较“市场化”了。销量最大的民办报纸要数《国华报》以及《越华报》,印数均达到万份左右。如今广州报纸的发行量往往以“十万”甚至“百万”作计量单位,但民国和抗战时期的老报纸,超过三千份的发行便属“大报”之列了,老广州以前称报纸为“新闻纸”,通常只有在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才舍得花钱购买,平日有常规购报习惯的人其实并不算多。《国华报》和《越华报》的优势在于“谐刊”(就是副刊),用武侠小说、趣味散文、名人逸事等生活化的栏目吸引读者,这种做法是官报所无法追随复制的。
至于小报,比较著名的有《探海灯》、《胡椒》以及《天文台》。小报风格各异,有专门翻译世界战争时事的,有揭露名人隐私的,也有攻击政府行为的,不一而足。
笔下风云
办报不息笔战不止
报纸是文人之间争斗的阵地和舞台,自从广州有了报刊之后,本地文人之间依靠报纸宣传自己言论以及打击“敌报”的笔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1901年到1911年,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中,相继出版的各类报刊约100种,相当于前60年所办报刊的5倍,形成了广州新闻史上的第一次办报高潮。光绪二十九年创刊的《羊城日报》是报馆兼营编译、印刷业务之始。在这次办报高潮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所办的报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先后在广州创办过《国民报》、《二十世纪军国民报》、《平民日报》、《可报》等15种报纸,在唤起民众、支持和拥护民主革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君主立宪派人士也在广州办起了《国事报》、《羊城日报》、《时敏报》等14种报刊。两派报刊围绕着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和如何看待清朝廷预备立宪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形成这一时期报刊宣传上的一大特色。辛亥革命之后,文人之间的笔战仍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则有所改变,例如在新诗和旧体诗的题材选择方面,当时的老派学者在报纸的副刊上公开抨击年轻人“不懂古文”,少壮派的诗人便立即揭竿抵制,先研究旧诗的特点,再用白话文的形式予以反击,两派支持者针锋相对,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行业组织
报界公会成政府智囊
广州的“报界公会”,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之一,成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地点正是设在西关。这个时候的广州,已经有数十家各类报纸,所谓群龙无首,报纸之间的竞争已现激烈态势,动乱的年代没有统一的监管,于是由民间组织的报界公会便顺理成章地诞生了。这个名噪一时的公会,来头并不小,发起人有《七十二行商报》的罗啸璈、《羊城日报》的莫伯伊以及《南越报》的苏凌讽等,这些人正是当时广州新闻界的“头面人物”。报界公会的工作是负责每日汇编所得新闻稿件,再分发给会员报馆,遇到社会政治重大问题则由公会议决方针,采取一致的步骤。由于工作得力,广州报界公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甚至市政府当局革兴市政的时候也经常向其咨询,可见其社会地位之崇高了。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杨湛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黄皓
下期预告:
从明代开始,纸行路就是手工纸作坊的集中地;清代时,这里还是八旗兵驻扎的区域,一般外人难以进出;纸行路走过一半,可以见到莲花巷,岭南文化世家——商衍鎏商承祚父子都是出生于此地,这也是纸行路的人文环境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
敬请关注下期《广州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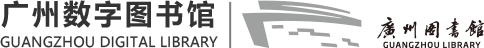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