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绪柏: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广州地理位置较偏,战乱不多,又是通商口岸,到清代,民间的财富积累也较多,都为刻书业的发展打下基础。其次就是社会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再加上嘉庆末年,阮元督粤,创立学海堂,粤人开始重视训诂考据之学,训诂考据重视版本,于是印书之风复盛。公私刻书日多,而坊刻也会承接一部分业务。在广州刻书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广东人参加科举,中进士、举人的数量也显著增加。
记者:书坊主要的业务有哪些?它们的出品有什么特点?
民国初年广州的书坊街
李绪柏:除了承接刊刷业务外,书坊也自刻书籍出版,也贩卖承接的公私刻书或者其他各家出版的书籍。所以书坊不但是书店,也集出坂印刷、业务于一身。书坊自己的刻书,就以民间日用的为主,少数名气大的书坊也刻过一些正史和子集名著,但数量不多。而且书坊也不止印书,因为主要是代表市民文化的,他们也会印一些年画之类,当时广东画家吸收了西洋画的技巧,不少作品就是书坊印刷的,还输出到东南亚一带,影响也相当大。
记者:书坊街的书坊是不是前店后厂形式的?
李绪柏:书坊街有一些书坊,但总的来谢,北京路一带有一个书坊的群落,并不只集中在书坊街一带。至于前店后厂,也不一定,有些书坊有自己的刻工,有些书坊实际上担任的是~个经纪人的角色,承担刻板印刷业务,然后委托给刻工,再将书籍拿回店里销售。
记者:书坊业衰落的原因有哪些呢?
李绪柏:最主要的是清末民初机器印刷传人,石印、铅印对雕板印刷的冲击比较大。另外,连年战乱,文化群体也四散,广州的经济地位也受到香港和上海的影响。而书坊业本身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也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地理展望
百座占书院三条书坊街将重现广州
广州市政府《关于保护大小马站、流水井古书院群的议案实施方案》指出,古书院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2002年10月,市政府已将这片旧城区内惟一尚存的成片古书院群纳入首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并对这批书院进行复建、改造和开发。由于拆迁安置任务重,投资大,并与周边开发项目不可分割,因此要分3期用8年时间进行保护、复建和改造。第一期是建设小马站书院传统风貌一条街;第二期建设流水井书院传统一条街;第三期完善整个区域的保护改造。届时,百座古书院和三条书坊街将重现羊城。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丹萍
图片摄影 本报记者邹卫
资料图片提供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
广刻趣评
袁枚:“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
有资料记载,乾隆年间,诗人袁枚曾经写信给在广东做官的弟弟:“又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字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可见广东(多集中在广州、佛山等地)坊刻当时确实水平不高,但胜在便宜,《子不话》之类的初级读物最有市场。
说文解字 书坊
又称书林、书堂、书铺、书棚等,是前人对书店的称呼。和现代的书店不同,书坊不但卖书,同时也承接印刷出版业务.因此,在中国古籍印刷与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广州的刻书业始乎何时尚难定论.但据文献记载,宋代广州已见雕版书。明清时广州刻书韭得到发展。至清朝中后期,“广板”图书闻名全国,广州成为中国刻书业的三大中心之一。
行业地理
近代广州文化传播三轴心:书坊、书局与书院
书坊街只是坊刻的一个代表。而坊刻又只是广东刻书业中的一小部分。查阅《广东省志》中《出版志》一册,有关广东的刻本,留下的全部都是官刻和私刻,也就是说,当年在书坊街卖的书,未必是精品,所以出版志中没有记载。
寻找书坊街并不是一件难事,在北京路一带,只要问人家卖金鱼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指得出来,只是没想到这条街如此之小。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书坊街以及坊刻这个行业的回忆,反而让我们更加感受到坊刻与城市发展的血脉联系,因为我们寻找的,也恰恰是正史之外民间的那部分。
坊刻胜地 书坊街
书坊街并不是惟一有书坊的街道,只是有幸以书坊为名,当广州的刻书业没落,它仍在城市的角落,悄悄记录着这段历史。
书坊街是一条不足百米的内街小巷,四五米宽,青石板铺路,没有机动车道,南端的巷口可见崭新的路牌,上书“书坊街”三字,北端有一座小小牌坊,横额写着“书芳街”。可见书坊街、书芳街只是一条,书坊是书店之意,而书芳则是对这条书店街富于情感的描述。在中国人看来,书也香,墨也香,这样一条小街,当年居然有十几家书店,自然是清香四溢。
今天的书坊街变成一个水族集市,似乎规模也并不大,也还是十几家店铺,主要是卖观赏鱼。这里没有书香,却也逸着些市井生活的怡然自乐。
除了曾是书店集中的街道外,书坊街另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小街的七号曾经是兴中会会址,不过现在痕迹全无,已经变成民宅,算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从清道光年间开始,广州的刻书业日渐兴旺,直到鸦片战争前完全衰落,在这期间,北京路一带遍布书坊,书坊街因临近提督学院,也是书店集中的地段,但却不是最多的。北京路、西湖路、十八甫路等内书店,有名号可查的就多达120多家。
书局大观 双门底
北京路始终是广州的一务重要的商业街,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街,双门底指的是北京路的北段(这个称呼不少老广州还知道),清末民初,这里集中了几十家书局。
《广州市地名志》中记载,清代耐的北京路从北到南分成几段,依次被称作承宣直街、双门底、雄镇直街和永清街龚阅《广东史志》我们了解到,原名永清路的北京路,民初改为永汉路,后来改为汉民路,1949年复称永汉路,1966年改称北京路——改名改得频繁。
在清朝,双门底集中了不少书店、文具店。清末民初,这里则集中了几十家书局,抗战胜利后,这里的文化商店又有所恢复,有20几家书局,广州市规模较大的书店基本工都集中在这里。当时,以汉民北路为中心,惠爱路、仰忠街、文德路旧书市场纵横交错,成为广州的文化中心。
解放后,北京路新华书店是广州市最早成立的一家新华书店,公私合营后,不少旧书局加入新华书店行列。由于书店原址是解放前的旧式砖木结构茶楼,上世纪80年代末,这里曾经被划入红线拆迂范围,后来经过改建,成为北京路的一块招牌。
除了新华书店外,今天的北京路仍有不少文化用品商店。较之百年前,文化用品的概念变化很多,单是买书都有很多渠道,整条街都是书店的情形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书院群落 越秀书院街/圣贤里
尽管书院刊刻的书籍与坊刻的有很大不同,但书院的兴起,带动了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发展。
与北京路相连的,有一条越秀书院街,背后就是大小马站街。街口有大的牌坊,走进去却没有多少书院的痕迹了。在西湖路的流水井,还可以看到完整的四进式的书院建筑,现在是一座幼儿园。在西湖路的小马站也可以看到曾氏书院大致的模样,现在是民居。
所谓书院,是指在官学和私人授徒之外的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既有官办又有家族兴办。广东的书院曾落后于北方,到清代随着经济发展、北方人才南下,在大小马站和流水坊形成了一个壮观的书院群。书院聚集人才,大兴教育,不但刊刻大量书籍,推动了广州的刻书业,使广东的文化学术在落后100年后再度赶上北方。
广州的书院群落是与广州的书坊业布局相呼应的,西湖路、大小马站街、龙藏街,既是:书院集中的地方,也是书坊集中的路段。
我们还找到一条东起学源里,西至北京路的内街,叫作圣贤里。圣贤里因明代学者黄瑜、黄佐居住在此而得名。黄氏家庭书香不绝,绵延400余年,黄佐更是广州著名的藏书家,在北京路建有藏书楼,清军入广州时化为灰烬。这样的街巷带给我们更多有关城市文化底蕴的联想。正是整个广东浓厚的读书气氛,才使书坊业这一民间的文化产业有了发展的根基。
坊刻名号 民营出版业三巨头
富文斋原址在西湖路,主人姓余,从嘉庆十八年开始即刻书,一直到民国。曾接刻学海堂、菊坡精舍的公刻业务,也曾经接印伍崇曜、陈澧等著名学者的著作。
翰墨园原址在双门底,主人骆浩泉。出品中有三色套印的《昌黎先生诗集注》、五家评本六色的《杜工部集》。
五桂堂原址在十七甫。由晚清落第秀才徐学成等兴办。民国初年在香港开设分局,所刻印的书籍远销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地区。广州五桂堂建国前歇业,香港五桂堂于1972年关闭。
地理链接
顺德马岗刊刻几近“苏板”
清代,广州虽为书坊集中之地,但工匠却不多,一般会将书板交给顺德马岗的工匠刊刻。马岗有不少女工从事刊刻,人工费较便宜、当时有苏州书商到广州卖书.顺便会到马岗刻书板,带回苏州印刷。江南不少作家都在马岗刻板,“见者以为苏板也”。
1934年,广东省编印局为补刻板本,曾经到顺德遍寻工匠,但会的人已经不多了、究其原因,顺德蚕丝业衰落,经济支柱倒塌,刻板收入低,所以这项工艺就烟消云散了。据中大历史系教授李绪柏介绍,曾有研究刻书业的学者到顺德寻访,刊刻工艺现在更是无影无踪了。
行业盛况 官刻坊刻各领风骚
中国历代从事刻书的,有官署、私家、坊肆和一些社会团体。官刻指的是各级官署所刻书,官府、官办书院,官办书局是刻书业的主体;私刻指的是私家出资资刻印的雕板书;坊刻则是书坊自己刻印的书。官刻与私刻的书主要是供给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至于村塾学生、一般±子以及日常生活的用书,则有赖于坊刻。
广州坊刻,以清代最盛,留存下来的书也较多。当时,广东刊印的书被称为广板或粤板。据《广东省志》中的《出版志》记载,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书坊,是乾隆年间广州的达朝堂。广州书坊有号可查的有120余家,集中在双门底(北京路)、西湖街(西湖路)和学院前(书坊街)等地,其余在十八甫、十七甫和龙藏街等地.也有规模不等的书坊。在众多书坊中,既有百年以上的老字号,也有仅昙花一现的宣统修《南海县志》曾记叙了书坊业的盛况:“道光中,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教上备省书客辐辏省城,至光绪而极盛。学海堂尝以双门底书坊歌命题、”直到1840年,书客裹足,“文武道尽”,书坊业才逐渐衰落。
名士雅集
早期出版编辑的学养
民国之前,编辑工作主要是古籍的辑集和校勘,是临时性的。在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刻书风气盛行,编辑工作曾经受到重视。主持学海堂编辑刻印工作的陈澧.陶福祥等人,以及为伍崇曜担任编订校勘工作的谭莹,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民国以后,随着出版方向从翻刻古籍转到以出版时入著述为主,编辑工作也从辑集古籍转为选择书稿、物色作者、书稿加工等方面。此后,随着刊物的大量出版,编辑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编辑已成为社会上的一种职业。
广板沿革
从手工刻印到机器印刷
广州现存最早的刻本
广州的出版业始于何时尚难定论,但据文献记载,宋代广州已见雕版书,南宋后期,广州出现了技术水平较高的刻本书,但数量很少。明代的官办书院大都刻书,崇正书院最有名,现仍有佳本传世,如《汉书》120巷、《四书集注》14卷等,是广州现存最早的刻书。
“广板”图书闻名全国
清代嘉庆以前,广州的出版业仍然比较落后。当时,广州刻书不多,且大部分是科举应用之书;至于其他书籍,则要外地运来。这种情况直到学海堂设立后才开始改变。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设立学海堂课士刻书之后,广州风气大开,宫刻、私刻、坊刻、社团刻蔚然成风。《皇清经解》、“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等卷帙浩繁、刻印精美、校勘详审的书籍。相继刊刻,“广板”图书由此乞闻全国。清代官刻以学海堂、菊坡精舍、广东书局、广雅书局最负盛名,私刻以伍崇曜、潘仕成为著。1823年回广州后的梁发则以刊印基督教小册子闻名,他于1833年用手工刻铅活字排印出中国最早的中文铅排本书籍。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广大学堂开办起,官立、私立、教会办学堂、学校大都自编出版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已不再局限于国学范围,而且大量涉及传自西方的近代科学。
民国时期的出版发行
民国十三年(1924)1月,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广州成了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不少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也设立非正式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大量政治性图书和学术专著,形成当时出版业一大特色。其中黄埔军校以其机构齐全、出书量大、发行网广而占有重要位置。
清广刻板书代表作:《海山仙馆》丛书
《粤雅堂丛书》(右)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济棠主粤时期,广州时局相对稳定,出版业又有发展。广州市区基本形成以永汉北路(今北京路北段)、文德北路、光复中路、十八甫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构集中地。其时经济建设发展,各类高等院校创办,大批反映经济建设的机关出版物以及致力于学术探讨的学校出版物,以量多质高构成这一时期出版业的一大特色。
本篇文字据《广州市志·出版志》整理
下期预告
今天广东的报业虽在全国独领风骚,却没有一条“报馆街”,而广州早期的报馆,却蔚然成行《中国日报》、《平民报》《国民报》《南越报》、《时事画报》、《羊城日报》《广东公报》…百余家大大小小的报馆,在当年喧嚣的第八甫、十八甫以、多宝路等商业街上风云际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喉舌敬请关注明日《广州地理》之“报馆街”。 敬请关注下期《广州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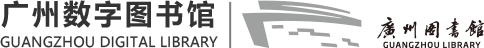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