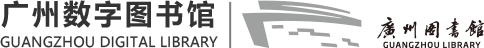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5-14
罗卓,字艮斋,新会人。曾学画于冯润芝,也习过西画。民国初年广东省第一回美术展曾塑六祖慧能巨像,因反响不错而移入白云山能仁寺。后曾到马来西亚经营锡矿,矿业失败后回到广州,从教于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其故居位于江门市棠下镇良溪村(原属新会)。广州沦陷后曾一度赴澳门避难,后返回新会教书,于1954年病逝。生有一子,名罗襄,善摄影,亦于“文革”中去世。后人评说其作品,善做佛像,与东莞李凤公齐名,亦善画猴。其身份亦有广东国画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之职,研究者则认为其并非其核心成员。
专家圆桌
艺苑通才,尤善佛像
广州画卷:提到罗卓,似乎这个人在广东国画研究会里面并没有太多记载,那其艺术方面究竟成就如何?
黄大德(美术史学者):在国画研究会里面,他的确没有参与国画研究会与岭南画派之间的争论。从其艺术成就来看,其画佛像尤为值得一提,功底细腻,用色非常独特,也很飘逸。他作画所用颜色鲜艳跳跃,他很多财产都花在了买颜料方面,一点都不吝啬。1921年广州第一回美术展的时候,他做了四组六祖慧能的巨型雕像,后来被移到白云山能仁寺,说明反应还是相当不错的。在艺术主张方面,他提倡“取自于眼前的实物,求其真”。
魏祥奇(广州美院研究生):由“广东与20世纪中国美术”编委会所编辑的《广东国画研究会》一书,刊载《广东国画研究会大事记》中称罗艮斋是为国画研究会前身癸亥合作画社的第一任社长。而且癸亥合作社最早发起者8人中即有罗艮斋姓名,或可感知其地位及影响。因其常隐遁于广州画坛,故记录不多,可知罗艮斋并非国画研究会之核心人物,但是为主干会员,与国画研究会中潘致中、程竹韵交情甚笃。罗艮斋善人物画像,其中以佛画像最佳。除此之外,罗艮斋兼擅花、鸟、禽、兽、鱼之类,以至与东莞李凤公并称“艺苑通才”,二画人之佛像画成就殊高,在当时赫赫有名。
身体力行的“中西调和”?
广州画卷:罗艮斋学过西画,会雕塑,学摄影,经过商,通过这些因素,他可能对中国画与“折衷”论题以及西画有怎样的看法?
陈继春(中央美院美术史博士):一个人的艺术成就和其生存状态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居派”笼罩广州画坛,罗艮斋学画于冯润芝,而冯氏的画学中又接受过沙面法国领事夫人的指导。此外,罗氏作为国画研究会的一员,与极得“隔山遗法”居氏弟子张纯初同是会友,他也能“撞水”和“撞粉”可说甚是正常。罗氏能雕能塑这一点和李凤公相同。要知道,绘画是平面的,但于此间可追求空间感;作为三维空间中存在的雕塑不可能像二维绘画一样以一个画面将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分割开来,由于雕塑与绘画共同的渊源,这有利于罗卓造型能力的锤炼。
魏祥奇:罗艮斋生活于20世纪初广州画坛,对于西方艺术形式和语言皆有详细了解,尝试制作雕塑和摄影有可能与个人的好奇心及兴趣有关。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罗艮斋与几乎所有中国画人一样,认为拒绝西方艺术形式是不可能的。在其年表中我们得知,罗艮斋曾与高剑父等画人组成“随社”,或可说明其并非与“折衷派”私人关系上有对立的可能,这与其恬淡的个人性情有关。另外由于其时政治、经济的混乱,颇多中国画人遇到解决生活基本需求的问题,对于罗艮斋从事商业活动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真正的传统守望者
广州画卷:罗艮斋的画学理念,究竟如何?
陈继春:罗卓在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授画时曾指出:“吾国画法,妙在神理,故初作宜师古,后乃取自于眼前实物,以求其真。”临摹是学习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尤其是“用笔”的方式之一,这一点至今在国画系的教学之中仍没有改变。
其实,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他的美术,都有他的绘画。中国画是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它是根据线条组织而成的,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线条就是中国画最显著的基本条件;中国画又以墨为基本,与西方的水彩画或油画以色彩为基本的不同,论画中以“笔墨”言之就是这个原因。
.jpg)
《龟图》
傅抱石曾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西洋画是写实的,而中国画是写意的;元代黄子久也拿着画本去山间写生,这就如西方画家一样写生、写实,但中国人写生和写实是将其看作学画的基础,而将之视为手段,不是把写实看作绘画的最高境界。西洋画是客观的,而中国画是主观的,这确是如您所说的是文化上的差异。
黄大德:其实国画研究会都是主张写生的,比如温其球、赵浩公、潘至中。他们经常在茶楼里面一面喝茶一面谈论写生。这与他们提倡的“临摹”并不冲突,临摹只不过是学习国画的最基本的步骤,和写生并没有什么冲突。有些艺术评论者在这方面是混淆不清的。
陈继春: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绘画也有临摹的。至于传统,很多人认为它和“旧”可以画上等号。实际上传统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不变的,传统的内涵不断地在更新和变化,而传统又必须实现现代的转化,故它应不是“一个传统的反叛”,而应是“转化”。
他们应该还会变得更重要
.jpg)
《熟蟹》
广州画卷:与国画研究会在当时的“重要性”相比,现在的“沉寂”,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您认为,以后他们还会再次变得“重要”么?
陈继春:20世纪上半叶新旧文化碰撞下的广东画坛中,“中学与西学”、“旧学和新学”的相持一直萦回,随着不断的思考,传统人文主义的“反衬”地位获得了根本的改变,国画研究会就是以相生的态势占据独特的文化领域。
国画研究会现在的“沉寂”或可以说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相信以后会再次变得“重要”。以罗卓为例,他懂摄影,他完全可以借助这一现代化的手段如某些画家一般去营造画面的光与影,但在其画中,仍是对线条十分眷恋。因为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国人,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于抵御“西方中心主义”是明智的,人们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之后,传统的人文又将被重新经典化。
画论
20世纪初的历史境遇·“传统”抑或“现代”?
20世纪初中国画坛一直纠缠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命题,几近形成怪圈:似乎所有中国画理论家和实践者,对现代中国画语言进行品评或自我言说时,便会毫不怀疑地使用和纠缠于这两个关键词。
中国艺术精神的“文本位”是“雅言”,倡导“以技近乎道”的哲思和审美理想。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亦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遇之后产生的矛盾。我认为实际最终要对抗的是“文人”的绘画观念:以美术作为变革时代的“工具论”的出现,必使“传统”丧失有效的时代话语权。而我们所经常讨论的“现代”、“革新”等命题更多与政治、科技、生产方式有关,将其推置于抽象、独立发展的中国画学传统,并不具备可参照的标准,毕竟西画与中国画迥然有别。但在这个语境之下,当时中国画人采取漠视和全面迎合的态度均无法立脚———漠视意味着“守旧”、“落后”;迎合意味着对中国文人心理的实质性伤害,肯定是被痛斥的。只有达到一种“共存”,才是符合“现代”之道的———“折衷”也就成为时代所造就的主流词汇。
20世纪初现代文化观念的介入,意味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生活中的人,在性情、思想观念展现出极大差异。个体的独特性,在思考自身价值判断时,取决于其社会地位、周遭利益关系等,甚至是一些破碎的情感和偶然因素。一旦需要表明自己的画学身份,便会被动地参与这种文字游戏:他们掌握了20世纪以来美术革命的语汇,之所以还要以“传统”作为另外一个标志身份,正因为完全的“西化”并非能够满足其某种内心的优越感。如果说清末文人们的大失落造成了他们倡导革新而追求“现代”的话,那么中国文人“传统”思想骨子里的抗争的确在一直压抑并释放。
很显然,无论继承或变革中国画,都必须在传统文化里寻找支持;他们也认识到只有依赖于“传统”,自身的“现代”才能够正统,才能够为中国固有的价值观所肯定。他们对于从西方他发而来的“现代”的接受在心理上是矛盾的,当猛然发现自己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标榜自身的“传统”质地似乎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手段。由“传统”变通到“现代”,文人们在社会心理情境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安慰和满足,而他们所宣扬的现代可能与自身的画学实践是脱节的。在中国画史中,谋求题材、样式、创作技法上的新意,也是经常发生的,西方文化的介入影响了中国的绘画行进路线,然是否就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差异呢?
《三国志》有言: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艺术趣味一直在进行一种循环往复的转换,似乎“传统”和“现代”都不能长久占据审美需要,就似天平,要维持一种量的平衡,要破除陈腐的“传统”或者追求“现代”趣味,那就彼此进行论争,直到达到一种合适的状态———并且这两种趣味观一定是相对的,而无法真正战胜对方,这种情况从20世纪初至今一直没有停息,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局面之相似并无二致。因此“传统”和“现代”在20世纪进程中哪个术语被凸显,都能够暗示出各自不同的时代面貌,“传统”也好、“现代”也罢,我们都不可否认其客观价值和实际影响:“传统”也可能“现代”,“现代”也可能“传统”。
(为广州美术学院研究所研究生)
魏祥奇
画作点评
.jpg)
《狸奴图》1937年,省博物馆藏,与赵浩公、卢振寰合作
款识:正轩道兄大雅教正,丁丑荷花生日,艮斋、振寰、石佛合仿北宋何尊师本。
罗艮斋兼擅花、鸟、禽、兽、鱼之类,多以没骨画法为之,设色淡雅明净,是受恽寿平、扬州派及海派影响,写意追求神趣。此帧着意于描绘狸奴之紧张情形,轻松、准确的用笔将狸奴蓄势待发的姿态跃然纸上。
画评:陈继春、魏祥奇
.jpg)
《佛像图》广州市艺术博物院藏
画中高手,善用白色者才是真正的高手。黄鸿光《品书录》中谈《说园》曾谈道,“我曾见过罗艮斋(卓)写的白衣观音,身上穿的三件白纱罗,三重花纹能够层次分明,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此幅作品,为艺博院所藏,另外其作品与赵浩公合作的《群猴》中白猴,也可见罗卓运用白色的功底。
画评:陈继春、魏祥奇
.jpg)
《采梅高士图》1922年作,香港艺术馆藏
此帧之“采梅高士”或可体现罗艮斋对传统文士生活的追慕与想象,与“新派”所倡导的题材要新直接相对。在制作中仍然以中锋用笔的勾线为主,注重“雅兴诗意”的人物情态描摹,是为魏晋以来人物画“传神论”的延续。在面部及衣纹处,淡设色以形成空间感,亦由顾恺之《女士箴图》中来。画评:陈继春、魏祥奇
乡邻评说
很纯的一个读书人
罗韬(羊城晚报编委、学者)
在我们那个村(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良溪村),画家有比他更有名的号称广东四大家之一的罗天池。罗艮斋晚年离开了广州,最后回到新会教书,正好跟我爷爷同事过。他不仅教绘画,还教手工,比如编竹篾什么的,很心灵手巧,他编的竹篾别人都舍不得用。
也有听说,他后来的生计很不好,本来他很有钱,但是都用来买颜料之类的,听爷爷说他其实是一个很文的人,不怎么懂生计,抗战时期我们村里断了侨汇,农业又不是很好,很多人过得很困难。我家里现在收藏有他和人合作的一幅扇面,是前几年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见到的,当时大概花了四千元左右。从他的画来看,很传统,这幅扇面也看不出他西画的痕迹。我家里还有一枚他的印章,他的字一般,印章稍好,但算不上大家,对于画家来说还算合格。画风很传统,以功力见胜,才气不算太大。很纯的一个读书人。
遗址寻访
良溪且留下
良溪这个名字,在最近几年因为后珠玑巷的缘故而重新变得火热起来。据说是南宋绍兴元年南雄珠玑巷起祸事,南迁领袖人物罗贵带领一干人等在江门棠下镇良溪村安家落户。沿着进村牌坊的路往前走不久,便是康熙年间建的“罗氏大宗祠”。村中老人,在被记者问及罗艮斋其人,唯有两三人可记得此人,只记得早已死去。其实这个村里更早以前出过一个更有名的画家,有粤东四家之称的罗天池便在此村。
.jpg)
破落残砖中塌下的一座房子便是罗卓最后生活过的地方。郭炳朋 摄
经由村支书的指点,在一个名为“韫石堂”的华侨故居豪宅旁边,破落残砖中已经塌下的一座房子便是罗卓最后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人当作放柴草的旧宅。听闻村里人说,最后的几年它就是在这里度过,并且病死于1954年左右,正是闹土改的时候。村里人嫌他长得黑,又有“黑面卓”一说。推开已经生锈的门,里面空无一物,唯有杂草。从里面的设施来看,他的晚年生活平淡,最晚关于他的公开活动则是1947年在广州参加的一次美展,和美展上很多人一样,该次之后,他基本上遁迹于画坛之外,成为一名教书匠了。
罗卓年表
1890年
罗艮斋生于广东新会,少就学于冯润芝。
年代不详,罗艮斋、邓剑刚、高剑父等创立随社。
1921年
广东省美术展览会开于广州,罗艮斋雕六祖巨像到会陈列:像之大,擬于小屋,而庄严肖妙,后移至白云山能仁寺供奉。
1923年7月
潘至中、罗艮斋等八人在广州创办癸亥合作画社。后邓芬等人加盟,共14人。并向省署呈请立案,罗艮斋为社长,画社同人每周于惠爱西路西园或城隍庙寰乐茶肆雅集,交流画艺,即席挥毫。
1932年8月
李居端受市教育局委任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新任校长,聘罗艮斋担任中国画系教务。
1933年3月22日
广州市校游艺会第四日,国画研究会加送该会会员作品200余幅到会陈列。书画名家到场即席挥毫者有温其球、赵浩公、罗艮斋、卢振寰等数十人。
1938年广州沦陷,罗艮斋避居澳门,以丹青糊口。
1947年1月2日广州黄图画廊举行美术展览会,参展者有李研山、赵浩公、罗艮斋、黄般若、卢振寰等。
1954年罗艮斋卒。
下期预告:卢振寰
本专题鸣谢:广东省文史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