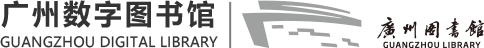马鼎盛、杨锦麟、曹景行,三位知名的学者型主持人,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三届”。
30年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改变命运走向的考试。考场之外,他们都曾遭遇过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种种波折。日前,“三剑客”一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30年前的旧事。
杨锦麟 给厦门大学写信“我要读书!”
◎口述人·杨锦麟
.jpg)
出生于福建厦门,198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厦大台湾研究所从事台湾问题研究。1988年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等职,长期从事时事评论。2003年初任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世界奥运行》等节目主持人,是华人世界中著名的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
那一刻,我们摆脱了噩运。
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570万人从田间地头、矿山厂房涌向了考场,那一场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
那是一代苦孩子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人们,对高考,以及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期待值,和我们已有悬殊落差。但我们挣脱羁绊追求自由,从三十年前的那一刻,已有了最起码的可能。
——杨锦麟
今年我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恢复高考30年的感言。我说:那一刻,我们摆脱了噩运。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报名被冷冷拒绝的那一个场景,原因无他——病退回城、家庭出身不好……
我还记得,给厦门大学招生办和历史系主任写的自荐信,最工整的四个字是:我要读书!
我也记得,1978年获得高考资格的喜极而泣,其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因狂喜而酩酊大醉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老三届”插队下乡八年
1968年,15岁生日那天,我随着上山下乡的大队人马,来到福建闽西山区的武平县插队。
临下乡前,学校发给我一张毕业证书,算是初中毕业。去除“文革”停课,以及初中第一学年的寒暑假,其实只读了八个多月的书,因此变成了“老三届”。
我一直找不到那张写满毛主席语录的初中毕业证书,家里人说,就在我下乡出发前,我一把将墙上那张毕业证书撕下,塞进炉子里,看着它在火焰里化为灰烬,还抛下了一句话:读不了几个月书,这也能算是初中毕业吗?!
武平县是闽西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当年毛泽东在闽西地区闹革命打天下,闽西八个县,他老人家走了七个县。武平县大概是太穷的缘故,据说毛泽东几乎没有在那逗留过。而我和我的同辈人,就在这个没有留下领袖足迹的贫困县呆了整整八个年头。
这8年里,我插过秧、犁过地、挑过粪、烧过瓦、熏过炭、养过羊、放过牛……总之,在那块土地上人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了。就凭那不足一年的初中学历,我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不瞒你说,那书还教得不赖。
很多知识,都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敲打出来的,点点滴滴积累,未必有系统,也未必全面。但那8年农村大学的阅历和学习,打下了人生起步的基础。
“白卷英雄”粉碎求学梦
这段知青岁月,给我记忆最多的只有苦难和挫败。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和“黑七类“的家庭出身有关。
第一次中专师范招生,我不由分说被刷了下来,传言很多,当然和自己不属于根正苗红有关。
1974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事件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紧张劳动余暇的休息时间。每天,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几个同学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起补习。但“白卷英雄”粉碎了我和很多知青的求学梦。
恢复高考之初报名被拒
1977年,我病退回到厦门,从知识青年的身份成了待业青年,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干起。
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多半是又脏又累的活。每个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每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一晚上没歇着,就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听说高考恢复的消息,我马上跑去报名,被街道办拒绝。第一,我刚以病退的名义回城,没有正式职业,政策不允许;第二,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我还是无法过关。
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我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只有20多天用来复习,但许多课程对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考生而言,其实压根就没有学过。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我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在酷暑中,扇扇子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能硬撑着,连裤裆都捂烂了……
政审不合格 政治考满分
焦虑等待之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政治分数获得了满分100分——一个政治审查还不能合格的人,政治考了100分,很具有嘲讽的结果;历史分数考了也是那年全厦门第一,其他成绩尚好,数学考得很抱歉,只有11分。
我的总分上了录取线,但由于诸多的原因,第一次录取未能上榜。扩招的时候,我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那封信里,写得最工整的四个字就是“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是那个年代所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呼唤,我能深刻体会到高玉宝的心情。
参加这次高考前,我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第二年,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100万港币的订单。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得的一笔大买卖!
与此同时,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要读书的心愿实现了!
我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工艺美术厂,迈进了大学校门。去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欢送。我喝得醉醺醺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中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子。那一晚,我喃喃醉语,翻来覆去说的就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少数幸运儿 多数底层人
30年前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是提供了一个人生选择。这个选择会让我们遭遇一个什么样的路向,无从预计。但是,这毕竟是我们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至少是一种解脱。因为,我们曾经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无助和无望。
和同辈人相比,当年能进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在77、78级的大学生中,有一部分成了社会精英。但我们这一代的多数人,现在依然是处在社会底层,承受着社会转型带来的痛苦,成了共和国从混沌走向光明中被牺牲、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这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些少数人的幸运。
因此,我想,反映高考30年,我们应该把当年没有机会参加高考的人也纳入视野。这亦是倾注一种人文的关怀。
马鼎盛 不“走后门”我上不了大学
◎口述人·马鼎盛
.jpg)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与红线女之子。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到1989年。1989年后返港定居。现为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十多年的报刊军事专栏作家。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马鼎盛
1967年,我在北京高中毕业。第二年,就跟着我哥到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了韶关山区的广东煤矿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我在厂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认为,上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被十年“文革”打断了。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
“小秀才”作文不及格
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它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
我们厂里有64人报名参加高考。那一年广东的高考,政治、语文、数学各算一门,地理、历史合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的两个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
考试的题目,我觉得不难。在韶关厂里,我是个“小秀才”,参加全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我六年来写过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高考写作文,不就像写个广播稿?我自信准能拿个高分。
没想到,轻敌了,我的作文不及格。那年的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考试时,2000字我一挥而就,不假思索。没看题目后面还有个括号,里面写着“记叙文”。而我把记叙文写成了论述文。
我是后来因为迟迟见不到录取通知书,查分时才知道自己高考作文是不及格的。
政审受到母亲“株连”
体检回来后,厂里有两个人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又急又不服气。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考试前,我还是辅导员,指导那两个人复习语文呐。
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了这事,说我不信自己的分数上不了大学。母亲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
大概厂里也比较同情我,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的分数肯定是没有问题。
仔细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当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想上大学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能经常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
副省长写信助我上学
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入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
杨老是个老革命,当时是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
学历史质疑个人崇拜
1978年,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为什么在“文革”中一些关照我父母的领导比如陶铸会被批斗?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时代境界。
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质疑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矛头直指“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从这个时候起,我的个人崇拜历史观才开始转变。
曹景行 还好第一次高考被刷下
◎口述人·曹景行
.jpg)
1978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后到香港,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主持《时事开讲》、《口述历史》等节目。
三十年前,我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下乡已快十年。我在那边结了婚、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以为我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然而,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曹景行(《口述历史》专访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刘道玉时感言)
1968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被分到安徽南部山区的黄山茶林场插队,当了10年知青。1977年,我在安徽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是体检时,我对医生说我得过肝炎,这一下被刷掉了。
那一年,在安徽农场里参加高考的人,考上大学的很少。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了;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地方学校去。实际上,在我看来,是安徽方面不愿意让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分到好的学校。
31岁才考入复旦大学
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没上,我觉得也不算失败。我的有些朋友把考大学当成改变命运的机会,看得很重;而我是觉得,有个读书机会就试一下,我没有那种“考不上,天就会塌下来”的感觉。
还好第一次高考被刷下来。1978年,我在上海参加第二次高考。这年招生“游戏规则”比较清楚了,可以填报大学专业志愿。我和同在农场的妻子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我进了历史系,她进了化学系。
本来我也想和妻子一样,报考理科。但是,考前我实在没时间复习。那时,我是一个农机厂厂长,每天忙到晚上10点以后,在蚊帐里看一两个小时书,就这么复习了一个月。考到后来,物理来不及复习了,算了,就报文科吧。如果能再给我十个小时复习,我就可以考理科了。
考进大学时,我和妻子都31岁了,孩子两岁,放在上海我母亲家里。我们在复旦读书时住校,周末回家和孩子、老人团聚。
涉猎广打下评论底子
在农村荒废了十几年,大学四年,我除了读书,没有别的想法。
“文革”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正因为刚刚开始,没有太定型的东西,给我们的空间很大,可以涉猎各种领域。那时,上课的内容比较简单,对我们来说,好多是以前看过的。于是,我有时间去多读一些其他系的课。复旦也给我们比较宽松的方式,选其他系的课,参加其他系拿学分的考试都可以。
大学时,我花了很大精力自修英文,把那些现在看来都很艰深的英文书拿来当教材看。我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那种《英汉小辞典》都被我翻烂了两本。把英文的基础打好后,自己就可以去寻找一个更大的知识空间。
我对经济、对美国、对当代时事更加关注。因此,我把读历史作为一个基础,同时也读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课程。大学毕业后,我进了社科院研究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
大学时候积累的知识对我日后做新闻也很有用。我做新闻评论的底子都是在大学时打下的。如果当时只是读单一的专业,知识面就比较狭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