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石牌发现晋代古墓
发布时间:2009-06-03 15:04: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
|
.jpg)
考古,今天和昨天的对望。图为现代考古
人员正在清理出土的人头骨。 CFP供图
旧闻回眸[一]
1928年
发现晋代古墓
按在那些噪音倾泻的城市街头,曾活跃着我们先祖的身影,一开始,他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当有光线从上面落下时,他们的生活被照亮了。他们张开眼,抬起头,站起来,成了人,从此,不再生活在脚下的黑暗中,而是尽最大可能向蓝色的天空延伸。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在黑暗和阳光之间,考古学是人类认识自身的神秘通道。光明在城市的上空,泥土与生命在城市的脚下。1928年3月,广州东郊石牌发现了一座晋代古墓。从旧报记载来看,此次考古虽语焉不详,却是我们的先辈对探知我们从哪里来的一次努力。
1.石牌发现古墓
据1928年3月31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石牌地方发现古冢一事,现颇引起一般考古学者之注意,且冢中之砖,每块皆有“永嘉九年”字样。“永嘉”为晋朝年号,故可断定谓传赵佗王陵寝之说不确。昨日,广东政治分会代理主席戴季陶先生谈及此事,表示将与中山大学方面共同研究。
解说:石牌古墓之所以引起政府相关人士关注,主要是因墓砖上“永嘉七年”的字样。这是一座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墓。
2.墓中物品多被乡人取去
据1928年4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员村乡民发现近代古冢一节,经志前报,查该古冢内之古砖,陆续发掘者,不下百余件。其砖身长约一尺,高约五寸,下黑上红,质重而坚,两边起有四方蓆文,底线水波纹,砖上有隶字“永嘉一年”,或“七、八、九年”等,及“子孙寿考”或“君子寿考”、“谏宜君子”等字样。独有一砖上现黄金色,砖面书:“永嘉七年”。一般考古家言,晋代司马炎之孙,于五胡乱晋时被胡人掳去,不知下落,想此处或为其避居之所在。此外,尚掘古剑钱币瓦鼎石狮多种,但乡人多秘而不宣,故无从查考,且多为黄埔乡人取去。现一班考古家,拟于今日联赴该村,切实考查。
解说:当时民众保护文物、文物属官有的观念甚为淡薄。
3.墓主或与司马炎之孙有关
据1928年4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番邑鹿步司员村乡,发现古墓一事,本报首先记载,记者以事涉考古,乘清明节之暇,特前往该处调查此事确切,但与前载微有不同,故特详细录出。
距员村约五里路之土名范家山,该山后右边之冈,野草漫山,从无有人知下有古冢。事缘日前有钟氏妇在该处采樵,偶践洞穿穴,足陷穴中,几不能拔,几费挣扎,始能拔出,俯瞰穴中,暗黑深漆,遂报乡人,前往发掘。则掘下有桥拱,以砖砌成。有冒险者,挺身入内,此穴为拱篷式,高八尺,长约三丈,阔仅一丈,是为长形,四周皆以大砖筑成,极为坚固,惟空洞无物。取砖考验,长九寸半,阔四寸七,厚一寸三,每砖重量约十斤,砖旁有凸字隶书,文曰“永嘉五年,辛未三子孙昌皆侯王”,永嘉元年丁卯,至七年癸酉均有,但以七年癸酉之砖最多。
一般人推测,古代流亡帝王陵墓,多不愿人知,故秘密经营,由元年至七年而成,故七年之砖独多,则此项工程,有数年之筹筑。考“永嘉”为晋朝年号,晋司马炎时代,因五胡之乱,流离迁徙,遗失一孙,是否即葬此冢,不敢臆断。明朱洪武之子,封永嘉侯,但用“永嘉”世号,可决其与明代无关,仍以晋冢为确切。
解说:古墓出土的墓砖显示,其朝代年限已初步可辨,排除秦赵佗王陵寝、明永嘉侯墓之说,墓主身份可能与晋朝司马炎之孙有关。
[二]
西村附近发现汉晋两代古墓
据1929年5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本市长庚路直通西村车站,由西村车站开筑马路,通至增埗,名为工专路。增埗之右邻,即工专学校,该学校之东边,即系坭城,查坭城为汉高祖时代使臣陆贾到越,招谕赵佗为汉时驻节之地,该处立有开越陆大夫驻节地址,石碑遍地,茂林修竹,风景颇佳。不日该路通车,游人必多。日前,工开筑工专路,在增埗村后,美华山冈,掘出晋代古砖甚多,砖上有“大兴二年六月始作”数字,极觉古雅可爱,砖旁另有字迹不甚明晰。
按大兴系晋元帝年号,据近一千六百余年,未知该处当时系何项建筑。工专校长,因此种古砖有历史关系,故即送广州市博物院陈列,以资考古家研究。
解说:这块名为“陆贾碑”的石碑如今依然保存于广州市博物馆。当时,发现这块“陆贾碑”时,广州市博物馆的前身广州市博物院(五层楼改建而来的)刚刚成立一年时间。
历史精神
迟钝的保护意识在伤害我们的文明
很多时候,我们对待历史文物的感情,是在“利用”和“破坏”之间交替选择,并用最直接、最经济的评价体系来评判文物:要么能生财,要么就是垃圾。无可否认,不少有价值的文物,正是在这种愚蠢、狭隘的观念下遭受着摧残,直至毁灭。
民国前期,军阀割据,国家大量文物饱受摧残,明十三陵、慈禧墓,每每被军阀视为生财的良机而被恣意破坏。窃国大盗横行的年代,国家都敢盗,遑论文物。或许真如某些人所言,与其让文物灰飞湮灭于不孝子孙之手,不如让它辗转流浪于国外,流浪或许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1949年后,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没见提高,相反,破坏手段倒更为隐蔽--各城市都是在建设新社会的旗帜下毁城灭旧,所谓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正是在这种建设思潮下,一些文物古迹,虽逃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却死于新社会的建设之手。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济利益的诱惑更是激发了某些人“利用”和“破坏”文物头脑——若古遗址、古文物能为经济创收,就把它塑造成城市的“脸面”,借它来充实城市历史文化底蕴;若是文物遗址已成为城市建设、经济创收的障碍,那就得为建设和创收让路。古物保护,没有了本能的珍爱,而更多成了某些人在利益权衡后的一种选择。
所以,尽管《文物保护法》已实施20多年,尽管近年来我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在增强,但各处涂炭历史文物的新闻依然屡见不鲜:定海老街区面目全非;襄樊古城墙夷为平地;福建三坊七巷遭到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历史建筑被拆光;南京一座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险些遭遇房地产拆迁生死劫;八达岭长城上的青砖被游客密密麻麻的刻字损坏;山东境内的齐长城被人极具创意地将底部挖空作商业铺面开发;《大旗英雄传》、《楚留香传奇》剧组损坏仙都风景区国宝级摩崖石刻和新疆唐代大墩烽燧;而在黑龙江宾县,一施工单位为了经济利益抢工期,公然对正在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的“纪家屯1号金代遗址”进行破坏……令人痛心的是,我国现在虽有101个历史文化名城,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里面,我国的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竟没有一个合格的。
贫穷和国人内心根深蒂固对文物的“贪念”是导致文物被大量破坏的根本原因。盗墓、挖文物营生的事在当代社会依然存在。湖南湘乡市水府庙发现了几个宋代砖窑,在当地文物部门赶到前,村民已将窑中珍贵的瓷器拿出去买卖,甚至肆意砸坏;山西临汾30座汉代古墓在违法施工中,先是被毁坏,后是被哄抢一空。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沉溺于一种焦躁急切的心态中,急欲改变民族的生存状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建设带给人民的利益着实丰富,也最有现实意义——你很难让住在大杂院的居民不认同现代化的生活,反而去关注老宅的文物价值,但核心问题是:当前文物破坏已发展到触犯社会正义底线的地步了,而这些不仅仅来自社会底层的“文物破坏者”,在他们心中,已没了对文化、古物以及对自己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敬畏感。
翻阅79年前的广州民国日报,看到一则有关“员村发现晋代古物”的新闻,忽然莫名其妙地感到奇好。古墓发现轰动一时,广州街头巷尾热议,政要学者重视,齐聚商讨对策……作为一个读报者,这种感觉是舒服的,尽管这种感觉因为带有时间和距离上的隔离,本身显得很粗糙且未必真实。
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的作家冯骥才曾说过,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在文化上往往会自我轻贱,会盲目抄袭强势经济国家的文化。可是,一旦你丢掉了自己的文化,那这个民族就会面临很大的精神危机,这比物质贫困还要可怕。
也许,只有到了文物、文化和文明几近消失的时候,我们保护文物的激情才会被触动。
□ 马羽飞
.jpg)
商承祚 殷周文字研究大家
商承祚(1902-1991),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广东省番禺县人。他出身书香仕宦之家,幼承家学,酷爱古器物、古文字,长大后师从罗振玉选研甲骨文字,后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在罗的指导下,于1923年21岁时即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
1927年,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兼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要成员的顾颉刚教授,聘请时任东南大学讲师的商承祚来校担任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教授。
商承祚教授在史学系开设了殷周古器物研究、殷周古器物铭释、殷墟文字研究、三代古器物研究等多门课程。顾颉刚教授于1929年初离校后,商承祚教授继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代主任。在该所顾颉刚为总编辑的《语言历史学丛书》中,商承祚负责考古学,陆续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及他自己集撰的《石刻篆文类编》、《金文萃编》等。
4.中大古学家商承祚探察古墓
据1928年4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 石牌鹿步司员村乡,蚯蚓尾山,又名樊家山,发现晋永嘉古冢事,经乡人迭次发掘,觅出古砖陶器多起。业经广东政治分会、省政府商议保护,先由古学教授商承祚先生等前往探视,带回砖器数方。
中山大学戴(季陶)校长因于十四日晨七时,约同政治分会委员黄绍雄、林云陔,省政府委员马祝万、许崇清、武观淇、黄季陆、傅汝林诸先生及助教,乘车前往详细勘查。途经中山公路(又称黄埔公路)直抵石牌乡,有石额门楼,再经德华潘公祠、两庵书院、过熏香畹董伯持先生处,由其向导前往员村乡。
登蚯蚓尾山,山并不高,若长坡然。该穴即在山腰,惟各器物及完整瓦石,均已无存,成一长方土坑形,长十一尺,阔八尺四寸,深约九尺许,尚有残碎瓦石、沙灰等物,散见浮土阁,穴之左旁,有一小穴,以竹探之,深五六尺,竹端触处,若覆有石灰等物,锄□穴底,声□□□,若□□□疑其下,或左右邻,当有更大之洞。
据向导熏香畹先生述,约当夏历间二月中旬,有樵者钟简夫妇在该地采樵,钟简偶出穴中,乡人□□,因之发现该冢全部由古砖砌成,中为一大窟窿,有四砖砌密门,砖旁有凸字隶书“永嘉五年”之义,最大一石门砖上则刊“永天下荒,予广州、皆平康”等字样,故审为晋冢。其间有一陶器及古剑,尽管掘者慎,仍毁败矣,□□□种古器,中山大学购得其一,存古物研究室中,藉供研究。
解说:由古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国民政府广州政要亲临古墓现场探察的举动可以看出,此墓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应。不过,查阅相关资料,有关此次考古与眼焉不详。
专家访谈
穗文物考古发掘始自30年代
李克义(广州市考古所):广州城文物的考古发掘大约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50年代开始比较有计划地从原来老城区往外进行勘探发掘。但城市考古一直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基建挖到哪里,考古才能发掘到哪里,考古工作不具有主动性。而且,由于城市建设需要或资金限制等原因,一些被发掘出的古迹遗址只好就地填埋,这有时也是令考古人心痛的事情。
好在现在广州市政府对考古工作较为重视,已组织了第四次文物普查。结果发现了大量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重要文物和3000多条文物线索,抢救了一大批行将被毁的历史文化资源。
此外,还准备将文物普查成果纳入城市规划电子地图,供城市管理者、城市建设者参考,以避免历史文化资源受到破坏,避免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
旧闻延伸
黄花考古队
1931年广州出现民间考古学团体
对于广州上世纪20年代的考古事业,广州考古界人士也难详说巨细。
有从事考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时,广州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概念,也没有类如现在的考古所部门,因此保留下来的相关考古记录和资料相当少。有些记载的是,1931年广州出现了一个民间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队,其时做过一些田野考古工作至于其如何运作,又发现并研究了哪些古物,详情不得而知。
据广州考古专家麦英豪介绍,古物的出土相比现代田野考古学引入广州还是要早一些。如1916年东山龟岗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木墓,因木板上刻有许多数字编号而轰动一时。国学大师王维国也为之写下专门的跋语。现代考古学的“几何印陶纹”一词也是由于该墓出土了一批印纹陶器而来的。
20年代,考古发掘已有章法
另由《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6月13日刊登的《发掘古物之进行》一文可知,政府当时对考古还是有章法进行规范和约束的。该文报道:由于近来中外人士常发起采掘古物团体并请领执照,外交部对此应付困难,因此制定“采掘古物条例”。这一条例除设定古物范围,规定了“凡埋藏地下之古物概归国有”,若在私人土地上偶然发现古物,发现人应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机关,转请国民党中央古物发掘委员会审查。许可者, 由内政教育两部发给执照,始可发掘。其不尊此手续者,无论为个人、为团体以盗窃论处。古物则由政府特别市政府咨明内政教育两部收存,并给发现者一定补偿金,或以市价收买其地皮保管之。
若要发掘古物,须先呈请地方主管行政机关中央古物发掘委员会之委员。发掘之古物,应由中央或中央所属学术机关妥为保存并予世界学者以研究之便利。该条例还特别强调:古物流通以国内为限,其有因事实上必须运往外国研究者,由内政教育两部会同发给护照,始得启运,并得由本国派遣专门学者随往共同研究,研究后须将正品运还。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马羽飞
.jpg)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中山大学考古学会会员合影。
.jpg)
1931年下半年,广州地区第一个民间考古学团体
——黄花考古学院成立。这是该学院成员的合影,前排左起:
曾传轺、胡肇椿、蔡哲夫。后排左起:谢英伯、杨成志、宋庭祜。
.jpg)
黄花考古学院的同人在研究大刀山晋墓出土的古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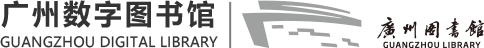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