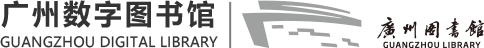所谓“宋诗理趣”,“理趣”是“文理之趣”,是蕴藏在诗文里面的脉理。宋代诗坛中名家苏轼,其诗文以用典多、才学化而著称,作诗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全不循章法,且对茶艺、书画、音乐、美食、方俗等等多有涉猎,这也造成了较高的审美门槛。
2024年10月19日,广图广州人文馆“唐宋诗词粤语讲座” 第七十六讲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粤听APP上线,主讲嘉宾石牛老师以苏轼的诗词作品为例,带领读者探讨当代诗文写作的藩篱与突破。
(以下内容根据主讲嘉宾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
错过音频直播?
没关系,
欢迎识别下方二维码,
收听音频回顾~

在我们印象中,苏轼的诗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是,我们日常读到的苏轼诗作,其实并不是他的主要风格,甚至不能代表他在古典诗方面的建树。且看下例:
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其一)
倾盖相欢一笑中,从来未省马牛风。
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
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
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
先说一点关于诗文题目的闲话。余以为,诗的题目一般有三种,一种是冗长的,如苏轼的:
游宝云寺得唐彦猷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书一绝句云山雨霏微不满空画船来往疾轻鸿谁知独卧朱帘里一榻无尘四面风明日送彦猷之子坰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叹前事因和其韵作两首送之且归其书唐氏
二妙凋零笔法空,忽惊云海戏群鸿。
清诗不敢私囊箧,人道黄门有父风。
题目很长,加上标点,则是:
游宝云寺,得唐彦猷为杭州日,送客舟中手书一绝句,云:山雨霏微不满空,画船来往疾轻鸿。谁知独卧朱帘里,一榻无尘四面风。明日送彦猷之子坰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叹前事,因和其韵,作两首送之且归其书唐氏
这个比正文还长了三倍有余的题目,叙说了一个小故事,还包含了一首别人的诗在里头。(唐询,字彦猷,曾知杭州。唐坰,唐询之子,初时上书支持“青苗法”,因此得到王安石赏识提拔,官至监察御史、同知谏院。后又在皇帝面前力陈王安石的不是,说他刚愎自任,不能兼容异议,最后被贬官。)
苏轼这诗的题目基本就是一篇小作文,读起来会有喧宾夺主之感,而这种情况在苏轼的诗集里比比皆是。
第二种题目就是有题目等于无题目,典型就是《无题》。实际上大部分的诗题也是这类,例如“秋兴”“山行”“送别”。这一类题目对于理解诗文内容、感受诗文的美,作用不大。这种题目更像是身份证号码,仅作为标识诗文内容用途。
第三种题目就是直接没有题目,例如《古诗十九首》,每一首就拿第一句的五个字作题目。类似的做法,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实际上古人作诗未必自撰题目,例如苏轼的《武昌主簿吴亮君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乃得其义趣,如见其人,如闻十二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六年闰六月》,这题目显然更像一篇后记或者小序,有些选本以之为题,也有些选本把这首诗题目写作《琴诗》。
这首诗也许很多人都读过,就是“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现在有的人评说宋诗的理趣,以此诗为例,实在谬以千里。这种诗只能算是机巧,在传统诗文中是不入大道,跟苏轼诗的真正价值相去甚远,也跟宋诗的理趣全无瓜葛。宋诗的理趣是“文理之趣”,而不是“奇理异趣”。何为“文理之趣”,后面会提及,这里先卖个关子。
对于这首《琴诗》,纪晓岚评价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个人基本赞同纪晓岚的看法。并且从中也可知,作者作诗,很多时候是不会自己编写一个题目的,而是后人为作者结集的时候编写上去。所以才有了上面的《武昌主簿吴亮君采……元丰六年闰六月》和《琴诗》这两种迥异的题目,前者出自苏轼之手本无疑惑,只是更像小记而非诗题,后者却似后人杜撰。
前人作诗不备题目,其实是老传统。多的不说,曹操写的那些乐府诗,题目就是乐府诗题,说白了就类似后世的词牌、曲牌,并不与正文印证。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诗人之中尚且有手书赠诗的雅事,也不会把题目特意写出来,通常是落款时写上“某年某日赠某某”,最多提及一点事由或者寄语。至于在书信中抄赠的诗作,一般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写上题目。
我们即将展开探讨的苏轼诗《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其题目属于第二种。表面上交代了事缘,实际上没有带来任何有效信息。题目不管是《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还是《和黄世仁戏赠马斯克》还是《戏题》还是《赠人》,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所以,我们直接跳过诗题,看正文。
首句:倾盖相欢一笑中
这里有一则典故,如下:
孔子之郯(谭),遭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甚相亲。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士不中间见,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有间,又顾谓子路。子路又对如初。孔子曰:“由,《诗》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今程子,天下贤士也。于斯不赠,则终身弗能见也。小子行之!”
大意是孔子出游的时候偶遇程子,两人“倾盖而语”,十分投契,有一见如故之感。
后世的邹阳在狱中写给梁王的求情信也引用了这个典故: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文中为了说明自己这个新来的门客也会对主子竭尽忠诚,便引用了“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谚语,后面又引用了一堆典故作为论据去说明这一观点。“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意思是:两人相识多年,头发都白了,却还是形容陌路,不能互相信任;而有的人只是道上偶遇,也能成为惺惺相惜的知交。
这篇是古文名篇,数年前讲授王维诗的时候,也曾提及“白首相知犹按剑”一语,亦出自本篇(另一段落)。此外,这篇文章的题目《狱中上梁王书》也不是文章原有标题,而是后人加上去的。原文出自《汉书》,只作引文,没有标题。
次句:从来未省马牛风。
“马牛风”出自左传,所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前人注解说:马逐上风而去,牛逐下风而来,故云不相及也。
这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出处,大意是马和牛背道而驰,走的道路并不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关联。
苏轼这两句诗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他跟友人)虽然是道左相逢,却一见如故。虽然大家走的不是同一路,却依然无妨成为知交。(另一种解法是:我们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人,而是同道中人)
十二年前我写过一首诗,“洗水新痕松雪绘,填壶熟气马牛刍”,正是引用了苏轼的诗意。这诗是一次去朋友的茶局,来自天南地北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人坐在一桌,一同品茶,高谈阔论,其乐融融。加上普洱茶茶气霸道,常致嗳气,如同马牛反刍,故一语双关,有“马牛刍”之语。
回到苏诗,首句苏轼引用《汉书》文章中记载的古谚,而此谚又出自孔子的言行;次句苏轼引用了左传的典故,我又引用了苏轼的诗意,这就是诗文写作中文化和知识的传递。千百年来,我们的古典诗文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在继承之余又各有生发,最后蔚为大观的。
作为读者,如果能读懂这里面一层又一层的意蕴,会感到如饮琼浆,滋味无穷。如果不能读懂,这恐怕也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读者要多读书、多写作实践。
颔联出句:卜邻尚可容三径。
这句包含两个典故,“卜邻”出自左传昭公三年: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大意是齐景公想让晏子换一所好一点的宅子,可是晏子不愿意,还引用了谚语“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意思是:好宅子不如好友邻,这跟“孟母三迁”的意思有共通处。
“三径”是说蒋诩的故事,他因为王莽夺权,免官归乡,便在家中竹林里开辟三条小径,与羊仲、求仲一起游玩,后面两人都是不求名利之人。这个典故通常用作“隐逸”、“逃名”的代表。作诗的时候,如果为了迁就平仄,也可以把“三径”写成“蒋径”。我自己作诗也多次引用过这个典故,其实合理用典是增加诗文厚度和质感的最佳途径,有的朋友因学力不足,便对这种写法妄加诋责,实在要不得。
颔联对句:投社终当作两翁
投社,庐山莲社杂录:“谢灵运欲投名入社,远公不许。灵运谓生法师曰:白莲道人将无谓我俗缘未尽,而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
投社就是投名入社的意思,苏轼在他的另一首诗里写过“投名入社有新诗”。
两翁,在苏轼同代诗人的诗句中经常出现,王安石、欧阳修、曾巩、贺铸等等都写过不少,大意都是“两位相知相识的好友,一同老去”之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白居易曾作《新丰折臂翁》,后陆游以此与塞翁相并,写了《两翁歌》,然与苏轼此诗并不干涉。
总的来说,颔联这两句意思是:我们如此投缘,可以考虑做邻居,天天游山玩水,与岁月共老。
颈联: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
《离骚》:纫秋兰以为佩。
《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
同样是引用,在上联的基础上深拓一层,表明他们二三知己结社,只是为了吟风弄月,追慕古人的雅逸情怀。
尾联: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
出句出自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这里特别指出,杜甫这诗只有五句,并非传抄错漏,而是本来如此。这类格式特异的诗,古代名家屡作创新,而到了今天,我们绝不可以故步自封。
苏轼之后,辛弃疾又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句诗引用下来:
辛弃疾《丑奴儿》:
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
君来正是眠时节,君且归休。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
这首丑奴儿跟另一首(少年不识愁滋味)用同样的韵字,却没有那首著名。实际这首词的审美价值绝不低于那首,只是审美门槛高了些。个人认为,辛弃疾这首词,并不逊于苏轼诗作,更不输杜甫原玉,诗人之间的传递和发展,是多么的有趣。
末句“白发年来渐不公”出自杜牧诗: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
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大意是世间公平的事太少,只有“白发”,无论贫富贵贱,年岁一到,具不饶人。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却没有一语落实,而是似实还虚,余音绕梁。
苏轼此诗,处处是对前人的引用,却又自如伸展,不受牵制。这些含蕴之间关系若远若近、似张似弛,反复把玩,滋味无穷。人皆谓“宋诗理趣”,在我看来,宋诗的“理趣”是“文理之趣”。是蕴藏在诗文里面的脉理,是那层层叠叠的留传,是那跨越世代的呼应。没读懂,只觉槁瘠寡淡,文深意复;读懂了,便觉无限生机,趣味盎然。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苏轼这种诗,可以说自带小众体质,本就不是普世的、不是写给普罗大众看的。这里说的并不单是内容或者题材或者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审美趣向。实际上,苏轼大部分的诗都这样,他作诗旁征博引,并且对茶艺、书画、音乐、美食、方俗等等多有涉猎,但凡阅读量少一些、知识面窄一些,都会构成阅读障碍。
苏轼腹中材料极多,作诗信手拈来,全不循章法。兼有天才,随意挥洒总能营气造势、鼓荡气脉。而作为读者,我的阅读趣味往往在此:读别人的诗,总能预判一二,乃至八九,唯独苏轼的诗,总不能预判他下一句会写到哪儿。
苏轼的诗,有一种足具厚度的松散感。这是审美门槛很高的,单是拥有学识才艺也欣赏不来,还得有足够的写作实践,才能一边读他的诗,一边会心微笑。这是真真切切的个人感悟,年少时我学识并不比今天差多少,却因为写作技艺没到家,也读不出苏轼的好。后来随着技艺的纯熟、审美能力的提高,才渐渐读出苏轼的好处,才惊觉苏轼的诗,实在大优于他的词作。
所以,苏轼这种诗,确实是小众的,是当今大部分人无法理解更无法欣赏的。然而我们今天课堂的讲题是“苏轼对现今诗文学习与写作的启发”,那么苏轼这种极小受众范围的诗作,又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时代总是在发展的。过去的另类,也许是未来的主流;昨天的小众,也许是明天的大众。
回顾一下中国诗文发展史,会发现:在隋唐以前,诗文的主要作者是世家大族、士大夫阶层。普通市民受教育的机会都稀缺,遑论写作诗文、学习艺术。唐宋始,教育资源下沉,这跟科举制的推行、印刷术的改进等等是同步的,其结果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阶层也参与了诗文创作。
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物资条件充裕,也让普通市民有了更多的精神生活需求,所以各种市民文学、市民艺术萌芽发展,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戏曲、小说等等,越来越兴盛发达。
从整个态势上,一方面稀释了诗文作者的综合文化水平。像《文心雕龙》所提出的形音义高度整合的审美标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代的许多出身市民阶层的诗人,也许并不缺乏学识,也具备天赋,却没有魏晋士大夫那种睥眇天下的视角,也缺乏全方位的美学教育。诗文从阳春白雪的堂奥之雅,渐渐变得世俗而可亲。而另一方面,新兴的市民文学也在侵蚀古典诗文的生存空间。
这种交融和争夺的结果是:像“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类的简短平易的诗篇获得了持久的关注度,成为现在的“名篇”。而像前面举例苏轼那种诗(其实那种才是苏轼的真正风格),在他活着的时候固然不乏知音(不然他不会酬赠那么多),可是在如今,却几乎是被埋没的。
以上,我们只是客观地整理古典诗发展变化的脉络,并不对之作是非优劣的评价。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未来会怎么样?
讨论未来,则先看现状。经过这三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社会富足了起来,大家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对下一代的美学教育也越来越重视,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人均报五六个艺术班,现在的小学生,往往可以把古人名篇倒背如流。可以想见,按照这个态势下去,在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的综合文化水平、他们的整体艺术修养,会远超我们,甚至超越宋代文人的平均水准。
像“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类的诗篇,不是说不好。它们的好处是简、浅、平、白,是个人都能欣赏。却正因为简单,所以一览无遗,所有的技法、含蕴、引用、意象……都毫无保留地摆在面前,让人无法生起反复探寻的意兴。这类诗,偶尔读一次觉得很好,读久了就索然无味;当不明白审美内在机制的时候读起来还能被感动,当明白那些机制,便毫无感觉了。
由此,我相信:当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从小接受丰沃的文化氛围,读了大量的各种诗篇,他们很快会对这种简单而直率的诗词生出厌倦,转而追寻那些复杂、精致、奥妙的篇章。苏轼的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最后渐渐湮没了。而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这种特质的诗歌会重新成为主流,成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茶余饭后的雅玩,成为二三知己传递情谊的贵物。
综上,从苏轼的诗,我们尝试窥探古典诗文未来的发展生态。而在更具体的层面,这门“垂垂老矣”的艺术,又会从哪个方向作出突破呢?李贺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方向。(后续的讲座将会继续讨论,敬请留意)
阅读延伸推荐:
1、《宋人诗话外编(上、下)》

【责任者】程毅中主编,王秀梅等编录
【ISBN】7-80049-252-8
【出版发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6.3
【载体形态】756页;20cm
【推荐理由】诗话是中国古代论诗的一种著作,在宋代非常兴盛。诗话种类很多,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概括为“论诗而及事”和“论诗而及辞”的两大类,是指评论诗歌、诗派、诗人创作得失和记载诗家故事的著作等,其体制有诗也有散文。诗话之外,宋人笔记中也往往有论诗的条目,前人也曾加以辑录,裁篇别出。本书收录的范围不限一格,从宋人笔记中辑出论诗的篇章,无论论诗而及事或论诗而及辞的都尽量收入,收录范围涉及一百种书,详尽广博,将宋人诗话网罗殆尽,供文学研究者参考。另外,在每篇诗话注以撰者简单介绍,颇省读者翻检之劳。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蔡鸿生藏书
【索书号】I207.2/228/1、2
2、《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责任者】顾随著,叶嘉莹笔记
【ISBN】978-7-301-14827-3
【出版发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载体形态】342页:图;24cm
【推荐理由】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先生,身为中国韵文、散文领域的大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长期任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著作甚多,是“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本书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珍藏60多年,第一次全部公之于世。顾随先生站在较高的人生境界,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文化艺术学术文化融会贯通,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感悟中国诗词的大境界,阐发中国古代传统的大智慧。本书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讲坛实录,庶可再现一位前辈学者半个多世纪前在讲坛上的风神情采、覃思卓识。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蔡鸿生藏书
【索书号】I207.2/2983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