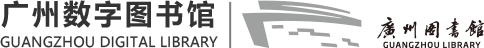广州图书馆中华经典传习所名家公开课
岭南先贤,往往因为偏安一隅行而不远,然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风范、节操及多方面惊人的才华却常使人心生叹服。9月7日“扎根岭南——本土经典文本导读”系列活动邀请到广州大学副教授李俏梅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凤莲,她们带领读者走近“菊坡学派”的创始人崔与之、“江门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陈献章、湛若水,与读者分享他们在学术、诗文及经世事功上独特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

崔与之、陈献章、湛若水三位先贤,或有师生之谊,或执师生之礼,代表了岭南学术、诗文艺术的高度,也是岭南学术、艺术薪火相传,走向繁荣的表征。从学派上来看,菊坡学派诞生于南宋后期,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儒家学派,崔与之是“菊坡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又颇有词章造诣,开岭南宋词之始,有“粤词之始”之称,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深远。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创立了名垂青史的“江门学派”,作为明中朝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是岭南地区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被后世称为“岭南一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这些评价和定位都是非常空前的。同时他独创的茅龙笔和茅龙笔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笔异彩。陈献章极力推崇崔与之,他有诗说“平生愿执菊坡鞭”,公开表示愿作崔与之的私淑弟子。又有《谒清献公真容诗文》说:“羊石卧古佛,仙游照福星。清风弥宇宙,白首拜丹青。先生宋代之名臣、吾乡之先哲,卷舒太空之云,表里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余,凝丞尊之而不屑,故能效力于当时,而全身于晚节。” 湛若水在考取举人之后拜陈献章为师。陈献章临终前一年将衣钵传给湛若水:“达摩西来,传衣为信,江门钓台亦病夫之衣钵也。兹以付民泽,将来有无穷之托。珍重,珍重。” 湛若水对先师也极为敬重,除了为其守孝三年之外,“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 用建书院这种广为传播的方式,兴教助学,把老师和自己的思想学问一起传递下去。湛若水也留下了对崔与之的称颂:“在天下为天下师,在后世为百世师,在一乡为乡党师”,这个称颂是至高无上的。三位先贤师徒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是令人仰慕的,它不只是一种感情,更是学术命脉的传递,这其中是有使命感的。
崔与之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乙科,开始为官之途。在任何一处,不管官位高低,皆留下好名声。文天祥评价他是:“菊坡翁盛德清风跨映一代”。他守淮五载,卫护四蜀,淡泊名利,激流勇退,七辞参知政事,十三疏辞右丞相兼枢密使。他能文能武,固边、平叛、仁爱、勤政爱民,头脑清醒,做事都能做到最好,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有人评价他是“始终无玷缺,出处最光明”。在学术上,他与学生李昴英开创、发扬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强调致用、务实、重惜名节。据说宋代曾有十卷本《菊坡集》流行,但经过宋末、元末两次战争,留存不足十之一二。
陈献章被后世尊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他少有才名,其老师说:“陈生,非常人也,世网不足以羁之。” 1466年,他以《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名动京师,人皆以为真儒复出。后会试不第,转而专心研习理学,居乡讲学,屡荐不起,后成为明代心学的奠基者。晚年他逍遥于自然,养浩然自得之性,心学思想体系臻于完成,他认为道和气为宇宙本体,心要去领会道,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以及“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
湛若水是是岭南文化学术思想的重要流派“甘泉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江门学派”的继承者和光大者。他27岁中举人,29岁拜师白沙先生。毅然焚掉“路引”(赴考证)以表学习的决心。白沙先生死后,湛若水为之服丧三年,并终生敬奉老师,传播老师学说。39岁中进士,与王阳明等相与论道,建立声誉。他的仕途比较顺利,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75岁致仕,游览讲学而归。在全国办书院近40所,对岭南乃至全国文化事业的推进贡献甚大。陈献章开启的心学,经湛若水更加完善化、理论化、精致化,并发扬光大,传播久远。人评如孟子对孔子的光大。他的世界观、基本观点师承他的老师陈献章,并做了一定的发展。他强调“随处体认天理”,以主敬为格物功夫,“在应对事物,心应感而发为中正意识,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天理。认为“道气”一体,“心在万物外,又在万物中”,陈湛心学是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说,跟王阳明的心学相比,没有那么激进。
值得指出的是三位先贤都是岭南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继往开来。崔与之被称作宋词之祖,清代的《广东诗萃》评价他的诗是“高华壮亮,有唐人遗音”,他开创了的“雅健”为宗旨的岭南词风,对后世岭南词人影响很大。陈献章生平不事著述,但颇有诗兴,流传的诗作有2000首左右,他的诗可歌可咏可教可观风俗,是诗教之楷模。《粤东诗海》评云:“理学名儒,多不以诗见长,而本性原情自然超妙。朱晦翁后推吾粤白沙一人。” 湛若水留下的诗虽不多,但能恪守师法,不好作道学头巾之语。“醞藉逸秀”,“颇得唐人古淡处”。
讲座最后,李俏梅老师还结合先贤的诗作《水调歌头题剑阁》《送范漕赴召》《渔歌子》《游罗浮》与读者分享了她的阅读感受:他们的作品风格清新刚健,极少萎靡之风。并且有岭南风物入诗,令人倍感亲切。在风格上又有着个性上的区别:崔与之诗笔力老健,感情真挚,词有雄浑豪放之美,近苏辛。陈白沙诗最多,各体各种风格都有,其中山水田园占半。他可以用诗歌载道,也可怡情,道理与性情能合一。湛若水诗较少,但重自然蕴趣,颇得师法,时有精妙。
今天讲座分享的三位先贤,在学术、诗文及经世事功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岭南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借用简又文先生的评价:他们“开‘岭学’之先河,树‘粤风’之楷模,使五百年来粤中人士之致力于学术、文学、艺术者,皆受其熏陶而养成一种力务朴实、潜心学艺、不竞声华、冲虚淡泊、独立自尊、抗节振世之崇高的风气,斯诚文化界之广东精神也。
推荐文献: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