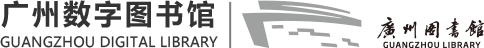清末民国文学家陈洵,少有才思,聪慧非凡,尤好填词,以诗词见赏于梁鼎芬,加入南园诗社。其著作《海绡词》、《海绡说词》,善用逆笔,神骨俱静,有“南有海绡,北有遁庵(张尔田)”之誉。2024年6月22日,广图广州人文馆“唐宋诗词粤语讲座”迎来第74讲。主讲嘉宾刘斯翰老师,将带领读者赏析陈洵词《玉楼春(新愁又逐流年转)》,共同感受陈洵深沉的爱国之情。
错过音频直播?
没关系,
欢迎识别下方二维码,
收听音频回顾~

玉楼春
新愁又逐流年转。今岁愁深前岁浅。良辰乐事苦相寻,每到会时肠暗断。
山河雁去空怀远。花树莺飞仍念乱。黄昏晴雨总关人,恼恨东风无计遣。
刘老师娓娓道来,声情并茂地为大家讲解陈洵的这首《玉楼春》。

刘斯翰老师开讲(摄影:胡霄)
《玉楼春》是陈洵的绝笔词。刘斯翰老师之所以在赏析海绡词时首先拈出它来讲解,一是想让大家真正读懂这首名作,二是想让大家体悟词里盈溢着的深沉爱国之情。
陈洵字述叔,号海绡,广东新会潮莲乡人。生于1870年,卒于1942年,享年72岁。陈洵一生没有考上功名,长期以教书为业,游历赣、豫十余年,偃蹇不遇。40岁回广州设馆授徒。1929年由词坛宗师朱彊村推荐,受聘为中山大学词学教授。1934年出版《海绡词》,达到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1938年广州沦陷。陈洵先是避居澳门,但因贫病交迫,1940年,陈洵不得已回到沦陷了的广州。当年7月,陈洵接受广东大学教职。后因咽喉癌,自次年4月便不再讲课。其所居海绡楼(连庆新横街11号)不久也被日寇强征拆毁。陈洵被逼迁居西关宝华正中约56号。国土沦陷之辱,外敌寇掠之凶,疾病缠身之痛,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陈洵悲愤交加,于1942年6月19日病逝于广州。
刘斯翰老师曾在《陈述叔晚年心境》中对述叔自澳门返回广州后的处境和心境作过剖析:
词人内心的痛苦是深切的,这从信札中可以见到:(信件一)
伯懃贤兄左右:正与家人开年饮酒,忽奉芳讯,兹情千里,新年风景,大非昔时,惟闭门差可无过耳,不独浓花野馆为可怀也。“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者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玉茗风流,千载如见,又孰知其言之深痛耶!韩树园近穷如何?黄七兄想安好也。晤时乞为我致候。率复。敬颂春祺百福!洵顿首 正月初二日
伯懃,姓许,名万雄,能书画,为广州国画研究会创办人之一,曾任广东高等法院秘书。日寇侵华,许伯懃移居澳门。其父许琴筑是陈洵好友。此札作于述叔初返广州之时,即1940年2月9日。当天是大年初二,粤人习俗,外嫁女于此日回娘家宴聚,称为“开年”。由于陈洵是刚收到许氏来信后,立即作复的,故其心境亦表现得特别真切。
初返广州,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横暴兽行,词人内心怆痛,而又无可告语,友人来信触动了这个“伤口”,他再也不能复忍,于是提起笔来,将郁积于中的感愤一吐而出。信中说:“新年风景大非昔时”,语虽含蓄,指意却十分明白。在一个有爱国心的人眼中,沦陷前后的广州是两个世界。词人一方面追怀往日过年,和朋友们到浓花野馆聚会;一方面却置身于关门闭户,避免飞来横祸的恐怖境地。感慨之余,他引述了汤显祖《牡丹亭》唱段中的名句,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者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汤显祖原意未必有如此深痛,而词人之心实痛,又叹息惜无人能诉!
述叔自澳归穗时正病黄疸,回广州后,就旧友德国医生柯道诊治,至七月始得痊愈。这在信中也见谈及:
伯懃大兄:音尘俱寂,忽复半年。澳居想如常?大小想皆佳也?仆闭门养疴,不闻外事。虽邻无二仲(注:东汉蒋诩,为兖州刺史,以廉直著称,因不满王莽专权,辞官归里,惟与高逸之士羊仲、求仲交往同游。),而亭草交翠,旧种梧桐渐高,晨夕相对,亦自欣然。辅以柯道医药,疾已去八九矣。澳中旧游犹在心目,竹屋风景无恙?兰初有见面否?伯任有无迁居?蔡伦事业近竟如何?愿一一详示。与君佩一纸,请加封寄去。率上,敬颂侍福不宣。洵顿首 七月三日
词人返穗后,仍住在连庆涌边的旧居海绡楼,闭门养病,心境亦稍稍平复。当时伯懃打算经营纸业,陈氏亦参与投资,庶几作为生活来源,“蔡伦事业”即指此。但此事未能实现,后来又改为经营海产:
伯懃贤兄左右:中秋、重阳两函并悉。霸才煮海,君子抱孙,一水盈盈,末由将敬,遥颂而已。鱼盐之举,虽愧昔贤,承公美意,敢不如教?前托抄寄词稿,未承惠复,想以为难矣。今欲使其不难,可将题目芟去,用小儿印字竹纸,作小行书,则一纸可了。《海绡说词》亦如之。分两函寄,尽从容也。敢以此请,勿却为幸。敬颂侍福,不宣。 洵顿首 先立冬三日
看来当初述叔之意,是打算隐居,靠投资许伯懃经商所得红利度日的。但毕竟远水难解近渴,所以,他的黄疸病刚好,就不得不接受广东大学的教席,并立即上课了。此信提到抄“词稿”和《海绡说词》的事,后来两封信都是为了这事,据此可知,述叔离澳回穗之际,并未将“海绡词卷三”和《海绡说词》稿随身带上,这可能是考虑到路途和返穗后恐有不测,亦似见离澳归穗之仓促,故并未预抄几份,以至事后要请代为保管的许伯懃抄寄。述叔获得伯懃抄稿后,才又亲自膳写了数本。

读者认真听讲中(摄影:胡霄)
述叔自归广州后即不复作词,除1940年应友人之托写《减兰·寄题八泉亭》一阕,借凭吊明遗民屈大均,表达了自己迫处日寇统治下的爱国情怀。此外,就是在1941年春作了绝笔《玉楼春》。写于当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廿五日)的信,可与此词相参证:
伯懃世台左右:别来再春,清明又过。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谓之何哉!得书知福履佳胜,韩六黄七复时相过从,甚善甚善。仲翔故宅仍为讲堂,丁卯廊高,室迩人远,时一经行,未尝不叹。绿肥红瘦,月浅灯深之为不可见也。(后略)
印证这封信札中所言:“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谓之何哉!”可确知词中“良辰”二句,是在指责当时那些趋附日伪政权的无耻之徒,他们不以国家沦亡为念,而照旧沉湎于征歌选色,寻欢作乐之中。信中特别用了“念乱”一词,这与词中“花树莺飞仍念乱”一句相同,并且形成对比:词人的心境截然不同。在“邦人诸友”视为的“良辰乐事”的应酬中,词人是“每到会时肠暗断”!他既不能公然地流露自己的厌恶,又如坐针毡,这是何等的痛苦。
就在写此信后不久,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喉癌发作,声音沙哑至于不能登台讲课。后是连庆涌一带被日寇征用,海绡楼遭拆毁。五月廿三日的信述之颇详:
伯懃世讲侍福:五月廿二日得手书,知月前曾有两函不达。黄氏礼费神代送,至感。承问登记,此事无关得失,不必亟亟,洵于此中已有阅历矣。海绡楼已毁,连庆一带极目萧条,惟有荒烟蔓草留供后人凭吊耳。《传》不云乎,‘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君如彼何哉?!’幸尚有屋可租,不然,则真如朱子所云:‘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也。’于十二日离连庆入宝华,连日料理书册,精神颇困。乃知琴书俊物,一经乱离,皆足为累也。公暇尚望多写数行,籍知异地亲朋消息。树园尤念,不宣。 洵顿首 廿三日
陈氏早年游食江右,中年归粤,始定居广州,赁屋而栖,教馆而食,生活虽然过得去,却并不富裕。后来,由于朱彊村的推介,受聘为广东中山大学词学教授,始能积蓄馀财,并于1929年终于购置了连庆涌边一所旧宅,亦即所称“海绡楼”。陈氏视之为隐居终老之所,尝与友人表示说:“七十以后,当辍讲闭门,闲居养性。”却想不到住了未足十年,就要离开逃难澳门,等到重回旧居年馀,又被逼迁,眼看着自己半生心血、终老托庇之所遭拆毁,夷为平地。词人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旧仇新恨,可想而知。信里专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话,指斥日寇如同夷狄的横蛮和企图永久占有中国的狼子野心。
龙榆生尝称是年冬获得陈洵一信,其中说:
洵澳门归来,再更寒暑,连庆桥宅,已毁于兵,移居宝华,又将半载。衰年多病,复逢世难,意绪可知矣。今春偶得一词,别纸写呈,聊当晤语。……相违千里,会合无期,北望新亭,此情何极。
信里,述叔亳不隐讳地表达了对日本寇侵略的悲愤之情,“新亭”的出典,就是晋末五胡乱华,中原士人流亡江南,东晋宰相王导鼓励大家同心协力恢复失地的故事。龙氏指出,“附词为《玉楼春》”。又说:“时予方收集《沧海遗音集》中诸家未刻之词……念惟海绡翁之作仍未备耳。因闻南中友好传言,翁有续词一卷,方拟自谋排印。爰即报翁一札,告以补刻《遗音》之意,乃迟之又久,消息杳然。”(见《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六号)如前所说,述叔于1940年底获得许伯懃代为抄寄的“海绡词卷三”稿本之后,亲自抄录了若干本。之所以始终未将它交付龙榆生,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卷词中,有鲜明的反日情绪,而龙氏当时投靠汪伪,用以印书的钱乃汪伪政权所出。陈洵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在此大是大非面前,他是不肯含糊的。
无独有偶,陈氏逝世后,汪精卫曾派广东大学校长林汝珩到陈家,向家人索取“海绡词卷三”稿本一册,并转交龙榆生处理。据陈氏在广东大学的同事熊润桐事后说,由于发现其中有反日情绪,结果使汪氏打消了为它出版的念头。
“海绡词卷三”稿本几经周折,直到1960年,才得以在台湾影印出版,此是后话。
弄清楚词人的晚年遭遇和悲愤心情,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这首绝笔词:
新愁又逐流年转。今岁愁深前岁浅。良辰乐事苦相寻,每到会时肠暗断。
经过上述对陈洵晚年心境的分析,这首绝笔词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据龙榆生说:“1941年冬得海绡翁书,附词《玉楼春》,翁自言‘今春偶得一词,别纸写呈。’”如前所述,词人于1940年春,因为穷困无法继续在澳门居住,只得返回沦陷后的广州,并于同年7月就任广东大学教席,词即作于次年春。“新愁”二句,意思是说:旧年被迫从澳门返回广州,成为日寇侵占下的“亡国奴”,也就是“新愁”。今年,这“愁”仍旧追随自己,不同的是,经过一年的“亡国奴”生活,这“愁”比去年更加刻骨铭心。“良辰”二句,对“亡国奴”的生涯作进一步描述:自己被裹挟着,不得不参加同僚们的寻欢作乐,但每到这种场合,内心的痛苦愈加剧烈!上片,词人用三个“愁”字、一个“苦”字,概括了自己回到广州一年的情感经历。更以“肠暗断”作出有力的宣示。
山河雁去空怀远。花树莺飞仍念乱。黄昏晴雨总关人,恼恨东风无计遣。
下片,词人转向上海那边的朋友们。在龙榆生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在本词前有小序曰:“酒边偶赋,寄榆生”。而在当时,词人保持书信往来的老朋友如张尔田、廖恩焘、谭篆青以及龙榆生等都在上海,也即“江南”。“山河”二句,词人借用南朝梁文学家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以及北宋词人晏殊《浣溪沙》词:“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怀念——“怀远”,和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念乱”。而“黄昏晴雨总关人”则是对“念乱”作加一重勾勒,并把对朋友们和对国家兴亡的关切牵合为一:
恼恨东风无计遣!
这里,词人把也是春天之物的“东风”用来比喻日寇。用“恼恨”表达自己对日寇的深切仇恨,以一个“遣”字,表达要把日寇驱除、赶走的愿望。而“黄昏”喻指词人年老,“无计”则是对于自己作为手无寸铁、百无一用的书生,被迫成为“亡国奴”处境的无奈和抱憾。
同是广东大学同事的诗人熊润桐,在日本投降、广州光复后曾作诗悼念陈洵。诗云:“一棺真继汩罗沉,愧我伶俜后死心。绝笔玉楼春竟去,遗音沧海梦中寻。东风已遣公何恨,宿草重论涕不禁。忍话覆巢前日事,几家梁燕尚栖林。”其中就特意指出《玉楼春》词结尾这一句的真正含意。

读者与刘斯翰老师交流(摄影:胡霄)
推荐书目:

推荐一:海绡词笺注
【责任者】 陈洵著 , 刘斯翰笺注
【ISBN】7-5325-3256-9
【出版发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载体形态】13,513页:照片;20cm
【推荐理由】是书分三卷,补遗一卷,收海绡词作二百四十八首,为《海绡词》首次整理出版,是为目前最为完善之本。海绡词学南宋词人吴文英(梦窗),词义隐秘难解。刘斯翰先生在笺注中特别注重对词的本事、异文、故实、出处、章法、词意进行阐释。读者可由笺注,而一窥海绡词之面貌。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刘逸生刘斯奋藏书
【索书号】I222/1638

推荐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责任者】龙榆生编选
【出版发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载体形态】234页;20cm
【推荐理由】本书是龙榆生先生长期研治词学的结晶,收录明末至晚清67位文人的518首作品,历来被公认为是研读明清以来的词的必备书目。书中收海绡词十一首。词作后附有作者小传,并采诸家评语。本书特别标出每首词韵之平仄,非常有助于读者了解词之韵律。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刘逸生刘斯奋藏书
【索书号】I222/1517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