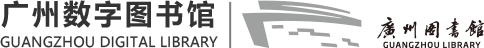扬州,古称广陵、江都、维扬,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美誉,自古以来便有无数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文中提及扬州。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让世人对扬州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十年一觉扬州梦”,大唐风流诗人杜牧更是以诗文将烟花广陵活色生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广图广州人文馆“唐宋诗词粤语讲座”第四十二讲——广陵秋深(上)于2021年12月11日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粤听APP上线,让我们跟随石牛老师的脚步,一起游览扬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以下内容根据主讲老师课件整理,仅代表其个人见解)

错过音频直播?
没关系,
欢迎识别上方二维码
收听音频回顾~
在广东人的观念里,南岭以北都是北方,长江下游都是江南地区,乃至经常把扬州和苏杭混为一谈。实际上,苏州、杭州、扬州,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色。这次我们先来聊一聊扬州的历史文化和诗词遗存。
提起扬州总觉得它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之都,若要仔细道来,又不知从何说起。杭州有西湖,有苏堤白堤;苏州有园林有评弹,那么扬州有什么呢?好像除了扬州炒饭和扬州修脚之外就找不出什么跟文化历史密切相关的点。实际上并非如此,论古诗名作数量,扬州实际上胜苏杭一筹。
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
论脍炙人口的程度,李白名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在今天必然是第一梯队,远比他在苏州写的《乌栖曲》著名得多。事实上,扬州的发展远早于苏杭。在汉文帝时期,受封吴国的刘濞铸私钱、贩海盐,最后起兵叛乱,其国都所在就是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城。当时的吴国虽然是封国,但幅员辽阔,大致囊括了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中部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不过跟“天下九州”的古扬州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古扬州甚至把江西、广东、广西都包括了进去。
汉初,广陵城经济繁荣之时,文化事业也是一马当先,邹阳、枚乘最初就是吴王濞的门客,这两人可算是两汉辞章先驱。而在那时候,杭州还没有西湖。西湖真正声名鹊起大概是白居易以后的事情了,李白也曾到过杭州留下诗作,然并非他的代表作,有《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文如下:
挂席凌蓬丘,观涛憩樟楼。三山动逸兴,五马同遨游。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嶂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傲云月,佳趣满吴洲。
这首诗虽然不乏个别亮眼的词句,但整体来说并不出色,尤其末二句,不免粗鄙浮夸,这里就不细加讨论了。
李白在扬州也流连过一些日子,写下《秋日登扬州西灵塔》,这个西灵塔据说就是瘦西湖北面大明寺中的栖灵塔,是与不是,难以考辨。这塔我们此番也去了,没发现与李白诗文相关的展示。但是按李白诗意,有登高揽胜之慨,而扬州无山,按唐时扬州城范围,唯一的登高望远点恐怕也就是这座塔了。
大明寺到底跟李白有没有关系不好说,但是跟另一位唐朝名人鉴真和尚倒是渊源甚深。鉴真是地道的扬州人,少年在长安实际寺受具足戒,然后回乡,二十六岁就当上大明寺主持。其后为了传教,他六次东渡日本,最后一次眼睛已经瞎了,总算渡海成功,并在日本站稳了脚跟,后来甚至为日本天皇授戒。鉴真对日本文化影响甚深。我们走在今天的大明寺内,看那风格别致的建筑,还隐约感觉到当年传教日本的文化回响。
李白在扬州写的诗还有《广陵赠别》和《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虽不算是李白的代表作,但有意思的是:李白在扬州没写出一流的篇章,可他在黄鹤楼作诗赠别无意中提及的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使得当今无人不知扬州城。这就是“佳句”的意义,黄鹤楼虽然是“主场”,但只有起首句轻轻带过,倒是忝陪客席的扬州因一句“烟花三月”而无人不识无人不晓。先前的课堂中我曾经谈到过,佳句重于佳篇,断无“有篇无句”之理,此处不妨佐证。
“烟花三月”,“烟花”二字生来便有一种纵逸的色彩。扬州因盐铁两便,又把控运河,历来是纸醉金迷之地。清朝诗人汪沆有七绝:“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说扬州跟杭州一样是销金窟,从此以后扬州保障湖才被人叫做瘦西湖,这个名字很形象,瘦西湖确实比杭州西湖瘦很多。相较于杭州西湖风景在湖周,苏白二堤斜穿而过,瘦西湖则只有三分之一是水,其他都是陆地,属于水道穿插景观。
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
唐朝是中国古诗的顶峰,四百年里名家辈出,若要论高低排座次委实不易。但如果有人问唐代诗人谁最风流,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牧,杜十三。风流是一个很难解的命题,它本是对美好事物的心醉神迷,可是重一分则沉湎,轻一分则淫狎;直一分则犷狉,迂一分则伪善。一句话:多情,深情,无情,缺一不可。关于这一点,杜牧在他的诗中自白得非常彻底: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情深如许,也让后世的痴男怨女们甚为追捧。可是诗中的“她”绝不是杜牧唯一钟情的女子,因为这首诗是《赠别二首》之一,另一首则是: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这两首诗不一定是杜牧诗歌的极致,但一定是杜牧风流的极致。杜牧多情不专,却情深似海;杜牧情深如许,却从也不沉溺。他在离开扬州没多久,就写下《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此诗字面上是杜牧追忆在扬州的时光,我们仔细一看,这里头哪儿还有半分对昨日红颜的眷恋思念,一门心思只牵挂那些逸游的快意日子罢了。对此,杜牧是十分具有自知之明的:
落拓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作这首《遣怀》时他已经离别扬州十年了。杜牧当时刚升任池州刺史没多久,池州在那时候已经升为上州,杜牧这官也算当得不错,但是他一向不拘小节冶游纵乐导致风评有瑕,这多少对他仕途构成负面影响。杜牧二十六岁中进士,任校书郎,虽然官职不高,但是这个年纪就高中进士,恐怕不止是“才华”二字。若以普通人家论,杜牧四十岁做黄州刺史,为一方父母官,也不算埋没,可对比先祖的显赫,还是差了点意思。所以我们仔细揣摩杜牧这诗,个中滋味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首句“落拓江南载酒行”绵里藏针,“落拓”二字断不可作穷困潦倒解,而应解作“放纵不羁”,这句多少带点牢骚跟愤世嫉俗;次句“楚腰纤细掌中轻”,这是对美好事物的赞叹,也是对当时生活的缅怀,只是这一句字面看似色情却绝无半点色情,关键在于杜牧缅怀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在扬州的生活中找到些许线索。
杜牧在扬州时间其实不长,也就两年左右。他在那里做牛僧孺的掌书记,是负责文书往来的僚官,清职。牛僧孺是牛李党争的牛党首脑,虽然当时失势当了个淮南节度使,毕竟还是跺一跺脚满朝震动的权臣,重点是牛僧孺赏识杜牧这个年轻人。在扬州这两年,杜牧的职位既没有压力和责任又能一展所长,个人生活上也有佳人相伴。所以这诗的前两句,是在和扬州时的生活对比,感慨由生。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的“觉”字现今多作“睡觉”解,但这里我觉得需要仔细辨析一下。
首先,诗中的“十年”断非指杜牧在扬州的时光,他在扬州不过两年,再怎么虚数也不可能有十年之数。也不大可能泛指他在江南地区担任僚属的时期,他在扬州呆了两年,然后在京一段日子,又去了宣州(今安徽南部)一年多,即便两段时期加上在京担任闲职的日子,前后不过五年之数。所以这个“十年”基本可以肯定是指他离开扬州十年之后的回顾。所以,这诗当写于公元845年前后。
然后,无论什么论点,若以杜牧仕途困顿作为论据,都是有问题的,他离开牛僧孺回京担任监察御史,以后稳步提升,40岁就当上黄州刺史,没两年到844年升任池州刺史,池州在当时已经升级为“上州”,杜牧的仕途已经向佳处发展了。同时,武宗禁佛也在845年,对此事杜牧是非常赞同的。在昭义军乱中,杜牧曾向宰相李德裕献策而得其所用,而这场危机也在844年成功解决了。按《新唐书》记载,杜牧虽然跟牛僧孺私交甚笃,与李德裕是敌对派系,但李德裕还是挺赏识杜牧的。所以这段时期的杜牧,最多只能说是嫌自己仕途不够通达而已。于是才有了后面两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头懊悔是有的,若他专心一意做官,怕未必输给祖父杜佑;可是楚腰纤细、扬州如梦,岂不是一种缅怀追思;最后赢得的薄幸名,个中有几分是懊悔?又有几分缅怀,几分自得?
最后,至于“觉”是“睡觉”还是“觉得”,两者都能说通,若作“睡觉”解,则是以过往十年为一沉睡,睡中只有扬州春梦,梦醒却面对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无疑这种解释更符合传统的“诗教”,其底层逻辑就是:认真做官才是正事,逸游不利做官,杜牧曾经逸游,那么杜牧只能表现出懊悔的思想。以这种解释的话,此诗的意味就只有“懊悔”,那么这首诗就成了杜牧对自己过往生活的批判,这当然是符合古代执政者口味的。这样问题就来了,只要懂写诗的人都能看出,前二句的情味是疏放有之、美赏有之、自许有之,却完全看不出丝毫批判的意味来。另一处疑点是:杜牧实际上并没有十年的沉湎,在他842年担任黄州刺史之后,当官颇为认真。
若按另一种解释:“觉”作觉得解。整句的意思便是:整整十年过去,才忽然觉得扬州的日子是梦,如梦般美好,也如梦般虚幻易碎,最终赢得一个又爱又恨的青楼薄幸名。这样涵蕴就非常丰富了,既有风流才子洒脱不羁的自许,也有光阴荏苒岁月不再的落寞;既有流连青楼笙歌美酒的怀缅,又有虚耗时光错失功名的懊悔。
是选取哪种解释,杜牧既然无法自辩,我们大可发散思维。一句话:艺术没有了多样性,就是一潭死水。总而言之,真正为扬州的文化意境砌造出城墙的,是杜牧。
扬州:诗中的禅智寺
除了“春风十里扬州路”,除了“十年一觉扬州梦”,除了“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的作品对扬州还有更深层的表现,如下:
《题扬州禅智寺》 杜牧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
这首诗在杜牧诗中不算一流,在唐诗中当然也非第一梯队,但依然是值得一读的诗篇。诗中体现出的娴雅婉静,仔细读来,是难得的享受。这首诗初读平平,实质每一句都精致无伦,更难得是精致却不纤巧。以我观之,“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是清流人语,“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是才子人语,“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是真富贵语,“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是风流人语,这一首诗,算是把杜牧的几个主要方面完美融合在一起了,其实是很值得反复咀嚼的。
杜牧此诗题禅智寺,关于这个寺院,还有张祜的《禅智寺》:
宝殿依山崄,临虚势若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
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乡思隔吴门。
此作稍逊于杜牧,弊在痕迹太重,但也是佳制,尤其颈联清气氤氲,最堪把玩。至于前四句攀描景物,虽然斧斤太重,但好在笔路清晰,作为今天学作诗的入门范本,有不错的价值。
张祜还有一首诗《纵游淮南》,名气其实也不算大,但是在扬州当地似乎颇为推崇: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可惜的是,这两座跟诗词名作强相关的寺庙今已不存,甚至不见有重修的计划。禅智寺已经被改作码头,只留一面粉壁,据说是新造;山光寺所在的茱萸湾倒是建起了景区,不过是由扬州动物园所用,至于遗迹,就只有一堵坏墙,上书“第一丛林”四字。这两处遗迹也不见有介绍相关诗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茱萸湾在入口处展现了另一位优秀诗人的诗作——刘长卿《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四首》。
赞